新药的故事.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1月24日
 |
| 第1页 |
 |
| 第10页 |
 |
| 第13页 |
 |
| 第30页 |
 |
| 第35页 |
 |
| 第60页 |
参见附件(1184KB,137页)。
新药的故事是由梁贵柏所著,我们一生都在与药物打交道,而药是从哪里来的,安全性如何保障,跟随作者一起,了解那些新药研发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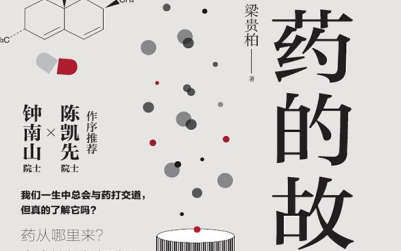
新药的故事作者简介
梁贵柏毕业于复旦大学本科有机化学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并获博士学位。梁博士在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工作多年,对西格列汀的研发做出过重要贡献,长期致力于中美医药界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中国医药健康事业的发展。
新药的故事内容介绍
我们一生中总会与药打交道,但真的了解它吗?药从哪里来?安全性如何保障?如何治愈我们?了解新药诞生背后的故事,才能读懂我们身体的健康密码,新药研发一线的科学家,带你重温人类挑战疾病的动人时刻。
在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中,平均每五人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我国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约9.89万例,且呈现年龄年轻化趋势。HPV疫苗的主要发明人之一原来是中国人……这是一本写给大众的医药科普读本,兼具专业性和趣味性,结合最新的数据,配以生动的故事,让严肃的医药知识不再枯燥,让有趣的人文故事更加真实。
“后抗生素灾难”年代,中国制药人应该有何担当?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之间该如何平衡?本书作者梁贵柏常年坚守研发一线,具备极高的学术素养,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丰富的从业经验,他分别从研发者和患者的角度出发,详细叙述了新药研发过程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这是一本深蕴人文关怀的药物发展史,帮助你理性看待疾病,多一点思考,少一分恐惧。
本书从一位一线科学家的专业视角出发,讲述了十余种对人类健康产生深刻影响的新药的故事。从广为人知的降压药,到如今备受热议的宫颈癌疫苗,从价格一度令人瞠目结舌的乙肝疫苗,到有望对抗多种癌症的抗癌药物,新药研发的历史也是人类对抗疾病的斗争史,本书以科学的态度、严谨的逻辑,再现了药物研发过程中的“黑天鹅”与“灰犀牛”。
新药的故事目录
第一章 一桩“赔本买卖”
第二章 人类与细菌的“军备竞赛”
第三章 为了一个没有河盲症的世界
第四章 遭遇“黑天鹅”的有准备之人
第五章 从后继专利药到更优专利药
第六章 当“头号杀手”遇上“头号大药”
第七章 “是药三分毒”的背后
第八章 凝结中国科学家毕生心血的HPV疫苗
第九章 挑战新世纪的健康威胁
第十章 默沙东的中国缘
第十一 章“不抗癌”的抗癌新药
新药的故事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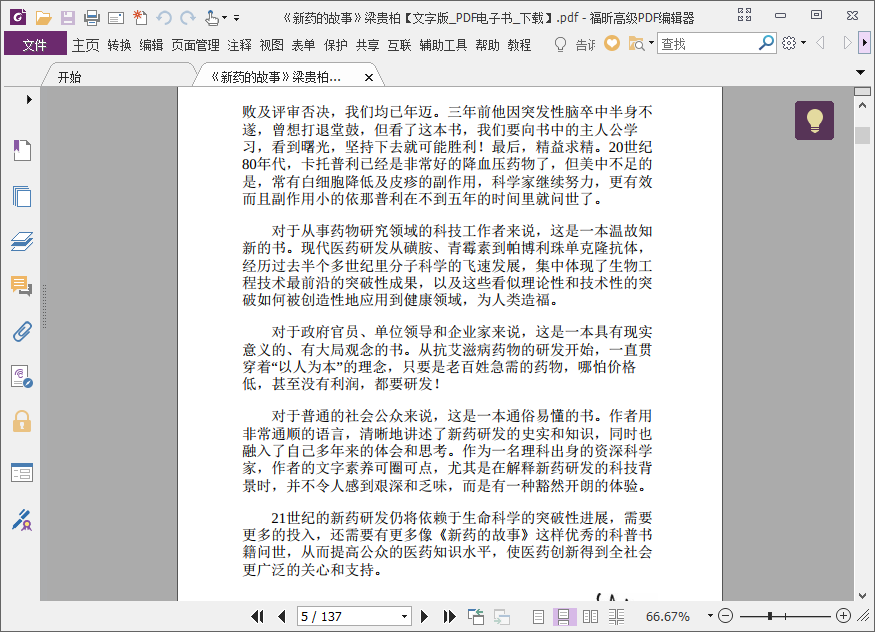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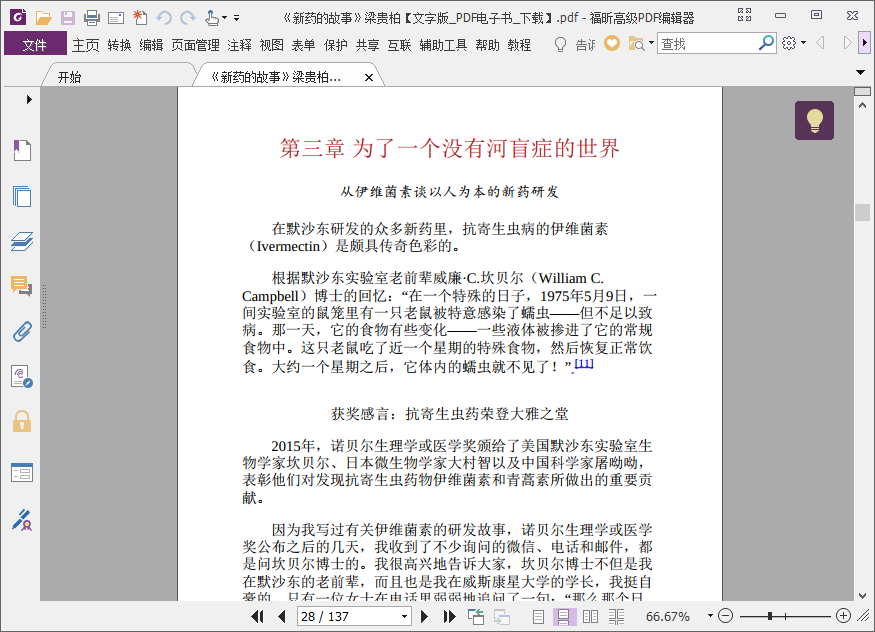
书?名 新药的故事
作?者 梁贵柏
责任编辑 刘免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76905
关注我们的微博: @译林出版社
意见反馈:@你好小巴鱼目录
CONTENTS
序言(一)
序言(二)
第一章 一桩“赔本买卖”
第二章 人类与细菌的“军备竞赛”
第三章 为了一个没有河盲症的世界
第四章 遭遇“黑天鹅”的有准备之人
第五章 从后继专利药到更优专利药
第六章 当“头号杀手”遇上“头号大药”
第七章 “是药三分毒”的背后
第八章 凝结中国科学家毕生心血的HPV疫苗
第九章 挑战新世纪的健康威胁
第十章 默沙东的中国缘
第十一章 “不抗癌”的抗癌新药
后记
注释序言(一)
我怀着强烈的兴趣阅读了梁贵柏博士撰写的《新药的故事》
大部分内容,对于目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药领域,这是一本不可
多得的科普好书。
作者梁贵柏博士曾经在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工作多年,是新药
研发第一线的优秀科学家。梁博士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和长
期向业界前辈们学习的体会,以生动的笔触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从
抗生素到抗癌生物药等对人类健康有着重大影响的药物,以及它
们跌宕起伏的研发过程。
新药的创新,我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也落后于印度和古
巴等国家。我们可以从这本新药研发历史的科普书中体会到创新
的真谛。
首先,药物创新是一个艰苦的历程。什么是创新的动力?我
相信每一个原药创新的科学家,在研究开始时绝不是先想到这个
药研发出来后会给他带来多少利益,而是出于对“未知的未
知”或“已知的未知”的强烈好奇心,以及对广大患者,特别是完全
无助、在当时无药可治患者的强烈责任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
初期青霉素的产业化,艾滋病、河盲症药物的研发一样。科学家
对未知的好奇心,永远是他们执着追求的动力。其次,创新总是
青睐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偶然发现一只黑天鹅不放过,更深入
观察,就得出天鹅不等于白天鹅的结论。科学家常常不轻易放过
意想不到的现象与实验结果,再深入探讨,就会有新发现。再
次,坚持与执着是创新者最重要的素质。君不见,在本书提到的
创新药物中,有哪个不是通过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
创制成功的?我和台湾地区的一位学者合作研发一种抗实体瘤新
药,在他研究15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25年研究,经过无数次失败及评审否决,我们均已年迈。三年前他因突发性脑卒中半身不
遂,曾想打退堂鼓,但看了这本书,我们要向书中的主人公学
习,看到曙光,坚持下去就可能胜利!最后,精益求精。20世纪
80年代,卡托普利已经是非常好的降血压药物了,但美中不足的
是,常有白细胞降低及皮疹的副作用,科学家继续努力,更有效
而且副作用小的依那普利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就问世了。
对于从事药物研究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来说,这是一本温故知
新的书。现代医药研发从磺胺、青霉素到帕博利珠单克隆抗体,经历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分子科学的飞速发展,集中体现了生物工
程技术最前沿的突破性成果,以及这些看似理论性和技术性的突
破如何被创造性地应用到健康领域,为人类造福。
对于政府官员、单位领导和企业家来说,这是一本具有现实
意义的、有大局观念的书。从抗艾滋病药物的研发开始,一直贯
穿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只要是老百姓急需的药物,哪怕价格
低,甚至没有利润,都要研发!
对于普通的社会公众来说,这是一本通俗易懂的书。作者用
非常通顺的语言,清晰地讲述了新药研发的史实和知识,同时也
融入了自己多年来的体会和思考。作为一名理科出身的资深科学
家,作者的文字素养可圈可点,尤其是在解释新药研发的科技背
景时,并不令人感到艰深和乏味,而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体验。
21世纪的新药研发仍将依赖于生命科学的突破性进展,需要
更多的投入,还需要有更多像《新药的故事》这样优秀的科普书
籍问世,从而提高公众的医药知识水平,使医药创新得到全社会
更广泛的关心和支持。2018年7月11日序言(二)
《新药的故事》经过作者辛勤的努力,即将付梓。我有机会
在出版前看到书稿,阅读之后有一种先睹为快的感觉,深感这是
一本难得的好书。
本书作者梁贵柏博士曾在美国默沙东公司从事新药研究十多
年,是一位新药研究领域的资深科技专家。他起初并没有想到要
写一本书,只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认识,写了一些散篇的新药研
究的“故事”。后来越写越多,越写越深,结集成册,就形成了这
样一本多侧面立体展现近代人类社会与疾病抗争历史画卷的书
籍。
这本书叙述了人类面对各种疾病挑战开展新药研究的探索过
程,这是一个各国政府、人民、科技界和全社会都关心的主题。
在当代,创新药物的研究与开发集中体现了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
领域前沿的新成就与新突破,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高新技术创新
与集成,是新世纪科技和经济国际竞争的焦点之一。20世纪下半
叶以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成果成为最激动人心的科学
成就之一。这些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使新药研究的面貌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推动药物研究与医药产业进入了一个革命性变化的
新时代,也使新药研究领域成为当代最受关注的科技创新领域之
一。本书讲述的新药研发故事,清晰地勾画了一些对人类健康产
生深刻影响的新药诞生的脉络,不仅涉及新药研究的科技问题,也涉及新药研究的方向遴选与决策、组织与管理问题,内涵深
厚,深入浅出。书中始终贯穿着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路、科学
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体现了丰富的学术内容、严谨的科学逻
辑。这些对于新药研究领域的科技创新必将带来诸多深刻的启发
和教益。这是一本讲述科学研究的书,但是它又不限于科技本身,而
是真诚、富有感染力地表述了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这既包括科
技工作者探索未知的好奇心,“攻克顽疾,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也包括讲道义、讲责任的真正企业精神,书中讲述的伊维菌素捐
赠和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的故事可以讲是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在这
里看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两者的结合
既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个人走向成功的必备要素,也是一个企业成
为“伟大的企业”的必由之路。
本书讲述了许多科学的史实和知识,但是并不艰深难读,也
不令人感到枯燥乏味。我打开这本书,浏览了开头的几行文字,就禁不住被深深吸引,很想一口气读下去。我想,这一方面是因
为作者在药物研究领域具有自身的创新实践和体验,而不是仅仅
停留在书本知识上;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他的文字素养。他能够
用生动、洗练的笔触,在清晰交代科技内容的同时,融入自己的
所思、所想,甚至包括人生的感悟,使内容有血有肉,也使文字
具备了一种隽永的风格。这就使读者的阅读过程成了一种愉快的
体验。
我在药物研究领域学习和工作了多年,看过不少有关药物研
究的书籍。我要说,这本书是非常独特的一本。我们读这本书,不仅可以学习知识,而且还能感受到人类的科学精神和不懈追
求。我相信这本书不仅适合药物研究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青年学
生阅读,事实上我觉得它适合更多人阅读,无论是政府官员、单
位领导、企业家,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都能从这本书中有所获
益。
2018年12月10日第一章 一桩“赔本买卖”
从抗艾滋病药物研发谈以人为本
60多年前,默沙东制药公司
[1]
时任总裁乔治·W.默克
(George W. Merck,1894—1957)说了一句名言,成为公司的座
右铭,一直被引用至今:“我们应该记住,医药是用于病人的。
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制药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利润,利润是随
之而来的。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一点,它(利润)从来不会失约;
我们记得越清楚,它就来得越多。”
[2]
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它讲的是新药研发机构和研发人
员以人为本的责任与义务。默克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默克先生同意将独家开发链霉素
的专利无偿退还给罗格斯大学基金会,与其他药厂共同开发和生
产链霉素,有效阻止了全球性肺结核病的蔓延。
[3]
默克先生认
为,制药公司对社会的责任以及与学术界的良好关系和密切合作
比任何一种新药的利润都更重要。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全球化进
程中,追求利润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同时也意味着不断地开拓
新的市场,不断地满足社会的需求。但是,如何把握眼前的利润
和长远发展、人类健康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始终困扰制药界的难
题。
艾滋病阴云笼罩
1981年,美国纽约和旧金山的医生几乎同时发现了一种新的
奇怪病症,该病的患者会被诱发出一些常见于有免疫缺陷人群的
感染和癌症,所以被称为后天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简称艾滋病(AIDS)。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而且当时缺乏治疗手段,病人经确诊后得不到
有效的治疗,死亡率很高,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相当大的恐慌。
医学界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1984年,美
国和法国科学家最先找到了致病的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简称HIV,又称艾滋病毒[AIDS
Virus])
[4]
,而如何有效阻止该病毒对人体免疫细胞的入侵,控制它的复制,并最终将其清除的重任也就义不容辞地落到了制
药界同仁的肩上。
1986年,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又称默沙东实验室[Merck
Research Laboratories])首席科学家爱德华·斯考尼克(Edward
Scolnick)博士宣布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默沙东西点研究所成
立专门的艾滋病研究室,研发抗艾滋病毒的新药,其他各大制药
公司也先后确立了抗艾滋病研究项目。然而,人们对艾滋病进一
步的认识给制药公司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主
要是血液传播、性接触(精液)传播和母婴传播,因此常见于吸
毒人群(交换针头)、同性恋者、性工作者以及靠卖血为生的发
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这样一来,不但抗艾滋病新药的市场将有
很大的局限,而且新药的价格也会受到相当大的挤压。默沙东制
药的内部资料显示,当时市场和财务部门对抗艾滋病新药的赢利
预测为负值。也就是说,即使默沙东的抗艾滋病新药研发成功,由于受市场和价格的限制,在其专利有效期内也不足以收回成
本。如果失败,当然是颗粒无收,全部投入都打水漂。因此,从
商业的角度看,无论怎么算,这好像都是一桩赔本的买卖。
“赔本买卖”
但“这不是一桩普通的买卖”,在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医
药、科学与默沙东公司》一书中,时任公司总裁的罗伊·瓦杰洛斯
(Roy Vagelos)博士写道:“太多的(艾滋病)患者正在死去,疾病正在蔓延,受感染的人群正在发生变化。……默沙东新药研
究院从上到下对艾滋病毒研究的专注以及公司对这个项目的投入之多都是难以置信的,尽管我们始终面临着彻底失败的威胁。”
[5]
这里当然有科学家对探索未知的好奇以及医药工作者征服疾病
的欲望,但同时也充分显示了制药公司及其员工以人为本、救死
扶伤的高度责任感和应尽的义务。艾滋病威胁着整个人类的健
康,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它的蔓延,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1989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科学家首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了艾滋病毒蛋白酶(HIV protease)的三维晶体结构,随后由美国
国立健康研究院(简称NIH)精细化,为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的研发奠定了基础。1993年,默沙东实验室成功地合
成了高效、高选择性的蛋白酶抑制剂——佳息患(Crixivan),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递交了新药申请(New
Drug Application,简称NDA),开始了佳息患的临床试验。同
年,为了攻克艾滋病,默沙东制药和14家制药公司联手,宣布成
立跨公司的合作,交换信息,共享资源,并尝试新药的组合治
疗。1995年,临床三期的结果显示,服用佳息患能有效地
(99%)降低血液中的艾滋病毒,与其他抗病毒药物联合服用
时,效果更加明显,可以把艾滋病毒降到检测极限以下。1996年
3月13日,继罗氏制药的沙奎纳韦(Saquinavir,1995年12月6日)
和雅培制药的利托那韦(Ritonivir,1996年3月1日)之后,默沙
东制药的佳息患作为第三种HIV蛋白酶抑制剂的新药上市,迅速
扭转了艾滋病无药可救的局面,死亡率大大降低,在很大程度上
消除了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慌。
佳息患虽然是第三种上市的HIV蛋白酶抑制剂,但它绝不是
一种仿制专利药(Me too drug),而是一种更优专利药(Me
better drug),受到医生和患者的一致好评,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
后来居上,全球的年销售额达到7亿多美元,超过了前两种HIV蛋
白酶抑制剂药物,占当时市场份额的40%。佳息患的成功不仅打
破了市场和财务部门当初对抗艾滋病新药的预测,扭亏为盈,为
公司创造了相当的利润,而且应验了乔治·默克先生60多年前的预
言:如果我们能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新药,帮助他们恢复健
康,利润就一定会随之而来。兵不解甲
佳息患等HIV蛋白酶抑制剂的成功,极大地提高了制药行业
征服艾滋病的信心。默沙东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兵不解甲,继续积
极寻找治疗艾滋病的新途径。
在学术界和制药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对艾滋病毒及其感染
和传播途径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除了HIV蛋白酶之外,我们又找
到了HIV逆转录酶(HIV reverse transcriptase,简称RT)和HIV整
合酶(HIV integrase)等新的靶标。艾滋病毒属于逆转录RNA病
毒,而HIV逆转录酶则是一类存在于部分RNA病毒中能以单链
RNA为模板合成DNA的酶,HIV整合酶则是帮助逆转录病毒把携
带病毒遗传信息的RNA整合到宿主细胞的酶,它们在艾滋病毒感
染(入侵宿主细胞)过程中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说起RNA逆转录酶的发现,这可是现代分子生物学中一个很
重要的里程碑,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学术界关于生命起源于DNA
的学说。回到20世纪7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Central
dogma)仍旧是:生命的信息先是从DNA转录到RNA,然后再从
RNA转化为功能和结构性的蛋白质。但是两位年轻的美国生物学
家——威斯康星大学的霍华德·特尔明(Howard Temin)和麻省
理工学院的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的新发现颠覆
了这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学说,他们分别独立发现的RNA逆转
录酶可以将RNA分子所携带的遗传信息反转录到DNA分子里,揭
开了RNA病毒感染之谜。1975年,特尔明和巴尔的摩共享了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后不久,耶鲁大学的西德尼·奥尔特曼
(Sidney Altman)和科罗拉多大学的托马斯·切赫(Thomas
Cech)又分别发现了具有催化功能的RNA分子——核酶
(Ribozymes),共享了1989年诺贝尔化学奖。由于这两项重要
的发现,原先被边缘化的有关生命起源的“RNA世界假说”逐渐成
为学术界的主流:最早的生命形式很可能仅仅依靠RNA来存储遗
传信息和催化化学反应,并以此完成自我复制。因为RNA逆转录酶由病毒自身携带,并且不存在于宿主细胞
内,所以它可以作为抗病毒药物的合适靶标。1998年9月,在佳
息患上市仅两年半之后,默沙东的依非韦仑(Efavirenz)就成功
地被FDA鉴定通过,成为首个上市的非核苷类HIV逆转录酶抑制
剂药物,为治疗艾滋病提供了新的手段,也为高效的“鸡尾酒”抗
病毒复方药物治疗奠定了基础。
默沙东的抗艾努力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他们锁定了下一个
靶标:HIV整合酶,一场新的攻坚战打响了。
整合酶志在必得
前面提到过,HIV整合酶是帮助逆转录病毒把携带病毒遗传
信息的RNA整合到宿主细胞的酶,它在艾滋病毒感染过程中也起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整个制药界早期所有寻找HIV整合酶
抑制剂的先导化合物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先后都放弃了HIV整合
酶抑制剂项目。制药巨头辉瑞公司的科学家在2007年还发表了一
篇论文,计算并论证了为什么他们认为HIV整合酶是最不可能成
药的靶标。
尽管默沙东实验室的研发团队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但是大
家没有轻言放弃,彰显了“舍我其谁”的豪迈。在经历了数次失败
之后,他们终于跨过了第一道“门槛”,发现了先导化合物,药物
设计有了一个初始的模板。在注意到了流感病毒的内切核酸酶
(Endonuclease)和HIV整合酶之间在生物化学方面的相似性之
后,默沙东的病毒学专家团队建立起了酶学筛选平台,有效模仿
病毒RNA的整合过程,然后从公司的化合物库里精心挑选了几百
个内切核酸酶的抑制剂进行筛选。他们不仅发现了一些能抑制核
酸链整合转录过程的二酮酸衍生物,而且这些二酮酸的衍生物在
细胞培养中也能相当有效地抑制HIV的复制,这在当时是从零到
一的关键性突破。
但是二酮酸衍生物不是理想的先导化合物,它们的化学稳定性不好,能与金属离子螯合,还有生物反应活性,用现在的术语
叫“缺乏类药性”(Lack of drug-like properties),公司内部也存有
不少怀疑的声音。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默沙东的药物化学
团队硬着头皮向前推进,竟然再次杀出重围,又开创出了一片新
天地。他们建立了有规律可循的构效关系,提高了先导化合物抗
病毒的抑制活性,而且还找到了能取代关键药效基团二酮酸的等
效基团,大大提高了“类药性”。
打开局面之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第一个临床候选药物,进
入了更加艰难、投入资源更多的临床开发阶段。一而再,再而
三,默沙东的前三种HIV整合酶抑制剂临床候选药物都出现了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被先后叫停。研发团队根据临床试验的信息反
馈,不断修正药物设计,完善化合物的体内外性质,终于将第四
种临床候选药推过了最后一道“门槛”。
2007年10月,默沙东新药艾生特(Isentress)通过了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鉴定,成为第一个上市的HIV整合酶抑制
剂。更重要的是,2011年12月艾生特被进一步批准用于年龄2~
18岁的人群的治疗,[6]
给未成年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以人为本
目前,对艾滋病毒的有效控制很大程度上仍旧局限于医疗条
件好的发达国家,因为在那里,患者有条件享受社会医保或购买
私人医保,可以严格地根据医嘱用药。但是在许多亚非拉发展中
国家,艾滋病还在继续蔓延,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统计,仅
2005年一年,艾滋病就夺去了300多万人的生命,其中约60万是
儿童。2012年,全球范围内被艾滋病毒感染的人群已高达3500万
人,主要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
[7]
在中国,被艾
滋病毒感染的人群总数虽然不多,但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上升趋
势,到2008年,艾滋病已成为导致中国人死亡人数最高的感染性
疾病。中国的医务人员必须努力提高民众对艾滋病的认识,积极地控制艾滋病毒的进一步扩散。
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和政府大都无钱购买西方大药厂
(Big Pharma)的抗病毒新药。尽管一颗胶囊或是一粒药片的成
本只有几毛钱,但药厂在研发过程中的投入却是天文数字,根据
最新的统计数据,开发一种新药的耗资超过10亿美元。所以,在
制定药价时,大药厂必须考虑其专利保护的年限以及市场的需
求,以期收回成本并有盈余。最后的药价与药片的生产成本基本
上是无关的,只有这样,制药公司才有实力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
入新药研发,我们才有希望攻克那些还在威胁人类健康的癌症和
其他疾病。然而,社会舆论却不这么看,时常一味地指责大药厂
为了追求利润“见死不救”,眼看着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人挣扎在
痛苦和绝望之中。面对这个两难的现实,默沙东制药再一次以人
为本,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努力把佳息患送到非洲国家患者
的手中。早在2000年,默沙东就开始与博茨瓦纳政府联系,大幅
度降低药价,然后通过美国政府、当地政府、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会(IMF)和各大私人基金会(如盖茨基金会),将佳息
患等抗艾滋病药物分发到非洲国家。
2001年,默沙东制药还率先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大幅
度降低抗艾滋病药物的价格,为整个人类的健康事业承担了应尽
的责任和义务。2005年,默沙东基金会
[8]
与中国卫生部签署了
全面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合作项目,并结成抗艾滋病合作伙伴关
系(China-MSD HIVAIDS Partnership,简称C-MAP),向中国
提供首期5年、共计300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偏远地区艾滋病的
预防与治疗。“关艾计划”响应卫生部的艾滋病防控策略,深入推
广“治疗与预防同步”的理念,及时更新一线艾滋病医生的诊疗知
识,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治疗和关怀。经过多年的努力,C-MAP项
目在提高一般大众对艾滋病的认知,提升政府卫生机构防治能
力,加强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关怀,降低疾病对社区产生的社会和
经济影响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荣获了2011年中国民政
部颁发的第六届“中华慈善奖”
[9]
,被誉为“最有影响力的慈善项
目”。每一个药物分子的价值可以用它的年销售额来估算,但它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制药工业救死扶伤,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崇高产业,也正因
此,和其他产业相比,它始终处于道德标准的显微镜下,容不得
半点“忽悠”。造假药、卖假药天理难容;研发了新药之后漫天要
价、见死不救,同样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中国的新药研发产
业来势迅猛,投入之多、涉及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快
速发展的过程中,希望中国制药界能以史为鉴,坚持以人为本,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2011年3月初稿于上海
2017年6月修改稿于新泽西第二章 人类与细菌的“军备竞赛”
从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到新型复合抗生素的研发
1942年3月14日,一个被细菌感染的病人接受了美国历史上
第一例青霉素治疗。光这一个病人就用掉了全美国当时青霉素库
存的一半,而生产这些非常难得的少量青霉素的厂家就是美国默
沙东制药的前身,当年的默克制药公司。
青霉素:从弗莱明的偶然发现到默沙东的大规模生产
青霉素(Penicillin)的发现是人类生存和致病细菌(又称病
原菌)的长期斗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928年9月28日,英国伦敦大学圣玛莉医学院(现属伦敦帝
国学院)细菌学教授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实
验楼的地下室里发现,他前几天忘了加盖子的细菌培养器皿中,长出了一种蓝绿(青)色的霉菌,而在这些蓝绿色的霉菌孢子的
周围,细菌的生长被抑制住了,形成了一个无菌的圆环。弗莱明
教授敏锐地判断出这些蓝绿色的霉菌孢子里一定含有某种抑制细
菌生长的化学物质,他将其称为“青霉素”。
这个很偶然的发现引起了细菌学家们的关注,但是由于没有
实用的生产线路,包括弗莱明教授本人对青霉素的研究都曾一度
中断。直到1938年,由英国牛津大学的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恩斯特·伯利斯·钱恩(Ernst Boris Chain)和诺曼·希特
利(Norman Heatley)领导的团队成功地从青霉菌里提炼出了抗
菌的化学物质——青霉素,才使得这一重要的发现造福于人类。
为此,弗莱明、钱恩和弗洛里共同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于青霉素比当时的磺胺类药物更加安全有效,马上获
得了整个医药界的热切关注。但是,青霉素的进一步研发却遇到
了很大的困难,除了实验室的小试之外,连车间中试都未能取得
成功,更不用说大规模生产了。当时的一位资深行家是这样进行
描述的:“那些该死的霉菌就像是一个坏脾气的歌剧演员,令人
难以捉摸,产率非常低,分离极为困难,提取更是要命,纯化简
直是灾难性的,测试也不可能令人满意。”这可不仅仅是他一个
人的看法,整个制药界都对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一筹莫展。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
大战。到了1942年3月,由默沙东生产的全美国的青霉素库存仅
够治疗两个病人,根本无法满足前线伤员救护的紧急需要。在美
国政府的组织下,默沙东与美国几大制药公司结为同盟,精诚合
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共同攻克了青霉素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这一
难题。默沙东制药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浸润式深罐发酵方法
(Submerged deep tank fermentation),大大提高了青霉素的产
率。1943年,默沙东制药新建成的青霉素车间共生产了42亿个单
位的青霉素。1945年,默沙东青霉素的年产量迅速增长到了6400
多亿个单位,满足了当时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大战场以及
美国国内的需求。青霉素的广泛和及时使用,大大降低了伤员的
感染,加快了伤口的愈合,减少了因伤口感染而不得不进行的截
肢和相关手术,使盟军的非战斗减员降低了10%~15%,对反法
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3年时仅有35人
的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当时名为Merck Institute for Therapeutic
Research)也发展为战后拥有500多名研究人员的大型研究机构,为战后现代化制药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链霉素:从“土壤之人”威克斯曼到默沙东的专利和技术转让
在青霉素被发现之前,细菌感染让人谈虎色变。肢体上一个
小小的创伤经常会因为感染而不能愈合,最后只能截肢,如果不
及时的话,很有可能会夺去患者的生命。细菌的历史比人类长很多,它们是这颗星球上的老住户了,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有细菌的“亲密陪伴”。但是,在农业文明
之前,人类与细菌基本上还是能“和平共处”的,那时我们的祖先
以狩猎、采集和游牧为生,无定居地,人口密度很低,零星的细
菌感染不可能有机会大面积地快速传播。农耕把我们的祖先牢牢
地拴在了土地上,谷物和牲畜的驯化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定居的
村落逐渐发展到集镇,人口密度越来越高,先前零星的细菌感染
在高密度的人群集居地有了广泛传播的可能性,再碰上传染性强
的细菌,就会发展成可怕的“瘟疫”,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整个村
落变成坟场,哀鸿遍野。早在公元前430年前后,就爆发过人类
历史上著名的“雅典大瘟疫”,持续了近4年,导致近半数的希腊
人惨死,几乎摧毁了希腊城邦。
因为细菌是微小的单细胞生物,用肉眼无法看见,所以人类
长期以来一直被这些看不见的小东西所困扰,把“瘟疫”视为“妖魔
作祟”或是“上帝惩罚”。直到1683年,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使用自
己设计的单透镜显微镜,在放大了约200倍之后,第一次观察到
了这些“活的小东西”(所以叫微生物),科学家们开始怀疑,就
是这些“活的小东西”给人类带来了疾病和瘟疫。其后的几百年
里,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直接或间接地把“传染性疾病”的起因与
这些微生物联系在一起,把它们称为“细菌”(Bacteria)。19世纪
末,著名的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罗伯特·科
赫(Robert Koch)确定无疑地证实了细菌可以导致疾病。到了20
世纪初,寻找抑制和杀死致病细菌的方法和药物已经成了医药研
究的大热门。
1938年,默沙东制药为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塞尔曼·威克
斯曼(Selman Waksman)的实验室设立了学术基金,用于土壤微
生物学(Soil microbiology)的研究。土壤微生物学在当时还是一
门新兴的学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得不到足够的科研经
费。默沙东制药公司的及时投入,使得威克斯曼教授的研究可以
顺利进行。1940年,威克斯曼教授的研究团队首先发现了放线菌
素(Actinomycin),根据默沙东与罗格斯大学以及威克斯曼教授三方的合同,罗格斯大学科研基金会将威克斯曼教授的放线菌素
发明专利转让给默沙东制药,由默沙东制药独家研发,于1964年
上市。威克斯曼教授最先把这一类化合物称为“抗生
素”(Antibiotics),这个名词很快被学术界接受,并在社会上流
传开来,成为最常用的医药名词之一,妇孺皆知。
威克斯曼教授毕生从事土壤微生物学的研究,从他的实验室
里先后发现了20多个新型抗生素,其中最著名的是1943年发现的
链霉素(Streptomycin)。链霉素的问世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因为那是当时唯一能治疗肺结核(Tuberculosis)的抗生素,威克
斯曼教授不但因此而荣获195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且还
成了《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被誉为“土壤之人”(Man of the
Soil)。
和放线菌素一样,链霉素的发明专利也归默沙东制药公司所
拥有,它理所当然地成为链霉素的独家生产者。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肺结核在很多国家开始流行,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默沙东生产的链霉素被视为“救命稻草”,给患者带来了希望,同
时也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是,在世界范围内,链霉素供
不应求,肺结核仍在继续蔓延,在威克斯曼教授的请求下,乔治·
默克毅然决定将链霉素的专利权退还给罗格斯大学科研基金会,这样一来,其他制药公司也可以从罗格斯大学获得许可,生产和
销售链霉素,共同抑制结核菌的蔓延。战败的日本是当时肺结核
流行最严重的国家,默沙东制药把自己的链霉素生产技术传授给
了日本人,为日本战后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默沙东制药
在链霉素的专利授权和技术转让中没有赚一分钱,但后来的发展
却让默沙东制药声名鹊起,成为最受尊敬的制药公司之一。许多
健康医药领域的企事业都乐意与默沙东公司合作,他们看重的是
默沙东公司以人为本、不贪图眼前利益的企业价值观。
抗药性:从进化论之必然到人类健康的新威胁
青霉素、链霉素等多个天然抗生素的发现,使人类在与细菌的“军备竞赛”中取得了显著的优势,细菌感染大多能很快被控制
住,不再令人谈虎色变。但好景不长,这个优势是短暂的,人类
刚刚从传染病和瘟疫的阴影里走出来,稍稍喘了一口气,细菌对
这些抗生素的反击战就已经初见成效——具有抗药性的变异细菌
被发现了。
抗药性或耐药性(Drug resistance)是指药物治疗疾病或改善
病人症状的效力降低。尽管抗药的细菌给人类健康带来了新的威
胁,但这也是进化论的有力佐证。
很多人以为抗药性是因为细菌对抗生素产生了某种针对性变
异,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有物种都在持
续不断地随机变异,在生存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个物种内
因为随机变异而产生的不同基因类型的分布也相对稳定,呈“动
态平衡”,最适应外部环境的基因类型总是在数量上占绝对优
势,被看作“正常”物种,而其他相对劣势的基因类型则被看作“变
异”物种。一旦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近年来的气候变化,一个物种内能耐热耐旱的基因类型相对于其他的基因类型就有了
优势,哪怕一开始只有一丁点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能耐热
耐旱的基因类型在此物种里所占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多,逐渐
被“富集”起来。如果气候变化再持续下去,它最终会成为占绝对
优势的“正常”物种,这就是达尔文所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一个物种能不能在逐渐变暖的地球上生存下来,取决于这
个物种内随机变异的基数是不是足够大,基因类型的分布是不是
足够广。如果基数太小,分布不广,能耐热耐旱的基因类型不存
在或者是达不到“可持续密度”,那么这个物种迟早会被淘汰的。
当一个物种,比如大熊猫,数量下降到一个临界值,它的基因类
型分布就会十分有限,对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就会很差,这就
是“濒危物种”所面临的困境。
细菌不是濒危物种,虽然抗生素的广泛使用给这些小东西的
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是细菌的基数足够大,基因的分布极
广,而且各种变异的出现又非常快,绝不是几个抗生素就能斩尽杀绝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青霉素使用之前,对青霉素有抵抗力
的细菌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在没有使用青霉素所带来的“自然选
择”压力的生存环境中,它们的优势不能体现出来,只能维持
在“劣势物种”的低水平。青霉素来了,给没有抵抗力的“正常”细
菌带来了灭顶之灾,但是极少数有抵抗力的“劣势”细菌活了下
来,并且把这种耐药特性遗传给了它们的后代,产生了有抗药性
的“变异细菌”。一代又一代,随机的变异不断地发生着,在抗生
素的巨大压力之下,不具有抗药性变异的细菌被无情地淘汰了,而大部分能产生抗药性的变异则“被选择”了。它们不断繁衍,抗
药性越强的基因类型越是容易“被选择”,所谓的“抗药性”也就越
来越强,给人类的生存和医药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挑战。
根据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研究人员的最新报道,[10]
目
前仅在欧盟以及欧洲经济区(EUEEA),每年因为抗药性细菌
感染而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3.3万,与此相关的医疗费用至少达
15亿欧元。2013年,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在《抗药性威胁》
的报告中称,美国每年因抗药性细菌感染而患病的人数超过200
万,其中至少有2.3万人死亡,与其相关的直接医疗保健费用估计
高达200亿美元,社会生产力损失更是高达350亿美元。在人口众
多的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无可靠的统计数据,但是
不难想象,在发展中国家里抗药性细菌性感染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应该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全球抗生素研究与发展伙伴(The
Global Antibiotic Research Development Partnership,简称
GARDP)2018年9月发布新闻称,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因抗药性
细菌感染而造成的新生儿死亡人数就超过20万。如何在全球范围
内有效控制抗药性细菌感染,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
碳青霉烯:从细菌抗药性的机制到默沙东的新型抗生素
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目前已知的主要有4种机制:
1.最常见的是,细菌把入侵的抗生素分解掉,比如耐药菌产生的β-内酰胺酶(β-lactamase)能分解包括青霉素在内的β-内酰
胺类抗生素的β-内酰胺环;另外,耐药菌产生的钝化酶(磷酸转
移酶、核酸转移酶、乙酰转移酶)可以使氨基糖苷类的抗生素失
去抗菌活性。
2.细菌自身发生的突变使得抗生素的作用靶点(如核酸或核
蛋白)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抗菌药物就无法或不易发挥作用,比
如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就是产生了青霉素的蛋白结合部
位的某些变异,降低了药物的活性。
3.细菌细胞膜渗透性或其他特性发生变异,使抗菌药物无法
进入其细胞内。
4.细菌的基因突变产生的外排泵系统(Efflux pumps),以主
动运输的方式将进入其细胞内的药物排出细胞外。
以分解青霉素的β-内酰胺酶为例,早期发现的内酰胺酶效率
很低,并不能很有效地分解青霉素,所以这些早期的抗药细菌在
青霉素压力下的存活率比“正常”细菌仅仅高了一点点。这些“一点
点”的随机变异在青霉素“自然选择”的压力下不断地被富集,被“优化”,直至产生高效率的内酰胺酶。为了制服这些能产生β-
内酰胺酶的抗药细菌,医药界的科研人员开始寻找不会被β-内酰
胺酶分解的新型抗生素,由默沙东制药研发的亚胺培南
(Imipenem)就是其中很成功的新一代“碳青霉
烯”(Carbapenem)类抗生素。
从概念上讲,研发耐β-内酰胺酶的新型抗生素不会很难,但
各大药厂的早期尝试都没有获得成功。“人算不如天算”,1976
年,当各大药企的研究人员还在不断摸索,到处碰壁的时候,默
沙东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从一种链霉菌的发酵液里发现了一个新型
的天然抗生素——噻烯霉素(Thienamycin),因为化学稳定性很
差,噻烯霉素的结构到1979年才被确定。科学家们发现它与青霉
素很相似,也含有β-内酰胺的核心结构,但是内酰胺并环上的硫
原子被碳原子取代了,另外还加进了碳碳双(烯)键,所以它被定义为“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这些结构上的变化使得碳青霉烯很
难被β-内酰胺酶分解,但保留了青霉素广谱杀菌的特性,正是医
药界苦苦寻找的新一代抗生素。从进化论角度看,碳青霉烯类抗
生素应该和有抗药性的细菌一样,也早就存在了,但从筛选技术
上讲,只有在抗药性的细菌被“选择和富集”了之后,能够杀死这
些细菌变异的天然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才有可能被发现,因为它们
反过来又被这些新型的耐药细菌“选择”了。
噻烯霉素本身的化学稳定性不好,不易于制备和保存,也不
适合于临床应用。但是,有了这个样板,“仿制”起来就容易多
了,而且目标也明确,那就是要发明一个比噻烯霉素更稳定,适
合于临床使用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通过一个很简单的化学修
饰,将噻烯霉素支链上的氨基保护起来,默沙东的科研团队合成
出了亚胺培南——第一个被批准用于临床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从此,人类与细菌的“军备竞赛”进入了一个新的轮次。
愈演愈烈:从“超级细菌”的发现到“后抗生素时代”
这一次,我们学乖了。我们无法阻止抗药性的出现,但是我
们可以延缓它的发生,延长抗生素的使用期。为了延缓针对碳青
霉烯有抗药性的细菌变异被选择和富集,发达国家对这些新型抗
生素的使用做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剂量与服用期必须严格遵守医
嘱,以保证其疗效,尽量避免滥用和误用。
但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医药管理制度不健全,缺
乏基础的医学常识教育,滥用抗生素的现象非常严重。到目前为
止,还有很多中国老百姓,不管是什么病,只要有头疼脑热,先
吃几片头孢(头孢菌素[Cephalosporin],另一种β-内酰胺类的
抗菌素)再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出现人们常说的“药吃多了,不管用了”。中国抗生素滥用的状况到底有多严重?中国药学会
发布的《2009—2011年抗菌药临床使用情况初步分析》显示,在
其样本医院中,抗菌药物占医院药品总金额的年平均份额为19.3%,远远高于国际一般水平。
早早晚晚,在多种抗生素的持续压力下,超级细菌还是跟我
们面对面了。
超级细菌并不是单纯地指某一种细菌,人们一般把对几乎所
有抗生素有抗药性的细菌统称为超级细菌,包括多重耐药铜绿假
单细胞菌、多重耐药结核杆菌、泛耐药肺炎杆菌、泛耐药绿脓杆
菌等。这个大家族的成员还在不断地被发现,并且越来越多。在
众多的超级细菌中,最著名的要数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名字太长,大家就把它简称为MRSA。最早的时候,青霉素
就能轻松搞定这种细菌,可随着抗生素的普及,没有抗药性的金
黄色葡萄球菌都被杀死了,剩下的都是有抵抗力的变异物种,能
产生青霉素酶破坏青霉素的药力。发展到今天,唯一有机会对抗
MRSA的只有万古霉素(Vancomycin)了。
后来,科学家们又在一些曾在印度接受过外科手术的病人身
上发现了一种含有金属β-内酰胺酶的超级细菌,这种细菌被命名
为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1(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1,简
称NDM-1),它与以往的耐药菌有很大的不同,复制能力很强,传播速度快且容易出现基因突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超级细菌,因此它的出现引起了医药界的高度关注。
2015年底,在一篇没有多少国人注意的科学论文中,华南农
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宣布从中国的细菌里发现了一种正在传播的基
因,取名为MCR-1,使它们能够抵抗现有的最强大的常常是作
为“最后手段”的抗生素。中国长期以来人口众多而又密集,人畜
之间的近距离接触相对频繁,这使中国成为新的感染性疾病的滋
生地。目前中国牲畜抗生素的用量(每头)是美国的三倍,占全
国抗生素消耗总量的一半。据信,最新发现的耐药基因就是在中
国的家猪中变异产生的。有证据显示,含有这种基因的耐药细菌
已蔓延到了老挝和马来西亚。
有科学家表示,一旦某种超级细菌在全球蔓延开来,人类将进入“后抗生素时代”。
所谓“后抗生素灾难”(Post-antibiotic apocalypse)指的是“泛
耐药性”超级细菌的普遍出现使得抗生素不再有效,感染性疾病
再次成为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这个说法许多年前就有人提出
了,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已经淡漠
了。其实它正在悄悄地降临,而中国极有可能是后抗生素时代的
主战场之一。很多微生物学家表示,目前的情况看起来非常不
妙,我们正在这场战争中失去阵地,所有的祸源都已各就各位,NDM-1、MRC-1等耐药基因在全球的蔓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也
许就是今年、明年或后年。
面对这场渐渐逼近的“后抗生素灾难”,制药人应该有怎样的
担当?
论持久战:制药人肩负重任
你也许会问,既然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始终存在,与用不用抗
生素无关,为什么滥用抗生素会恶化抗药性的问题?这主要是一
个轮次的问题,细菌每隔几小时就繁殖一代,使用抗生素越频
繁,细菌被选择的轮次也就越多,抗药变异的富集也就越快,所
谓的“抗药性”就越强。
另外,严格控制抗生素的使用,还能使已经有抗药性的细菌
自动退化,失去抗药性。在抗生素的压力下,不含有NDM-1、MRC-1等耐药基因的细菌是劣势物种,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一
旦它们生存的外部抗生素压力消失,就能反客为主,重新成为优
势物种,而那些能产生β-内酰胺酶的耐药性细菌就没有了优势,原来是生存的必需,现在却成了消耗能源的累赘,它们反而成了
劣势物种,失去了竞争力,繁衍几代之后就被边缘化了,回到先
前的以不耐药细菌为主的自然分布。这有点像超级大国军备竞赛
中的“裁军谈判”,双方销毁核武器,回到常规武器,因为维持一
个时刻准备着的庞大核武器库是很消耗资源的。可见抗生素的使用是很有讲究的,要规范化。什么情况下
用,用多少,用多长时间,都应该严格遵照医嘱。目前默沙东制
药正积极协助中国相关专业协会,支持中国更加规范地使用抗生
素。
亚胺培南的上市使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研发成为医药界的一
大热门。为了提高亚胺培南在人体内的半衰期,延长药效,默沙
东又推出了亚胺培南与西司他丁(Cilastatin)的复合抗生素——
泰能(Tienam)。作为对付抗药性很强的“超级细菌”的重要手
段,泰能是经验性治疗(医)院中重度感染的一线用药。2001
年,默沙东又推出了新一代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怡万之
(Invanz,学名厄它培南[Ertapenem]),为制服“超级细菌”提
供了新的武器。
变异自始至终存在,进化永远不会停止。
无论是“军备竞赛”还是“裁军谈判”,人类与致病细菌之间的
战争均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持久战”。为了人类的健康事业,医
药领域的科研人员始终活跃在抗生素研发的第一线,为人类的健
康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2年12月初稿于上海
2017年7月修改稿于新泽西第三章 为了一个没有河盲症的世界
从伊维菌素谈以人为本的新药研发
在默沙东研发的众多新药里,抗寄生虫病的伊维菌素
(Ivermectin)是颇具传奇色彩的。
根据默沙东实验室老前辈威廉·C.坎贝尔(William C.
Campbell)博士的回忆:“在一个特殊的日子,1975年5月9日,一
间实验室的鼠笼里有一只老鼠被特意感染了蠕虫——但不足以致
病。那一天,它的食物有些变化——一些液体被掺进了它的常规
食物中。这只老鼠吃了近一个星期的特殊食物,然后恢复正常饮
食。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它体内的蠕虫就不见了!”
[11]
获奖感言:抗寄生虫药荣登大雅之堂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美国默沙东实验室生
物学家坎贝尔、日本微生物学家大村智以及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表彰他们对发现抗寄生虫药物伊维菌素和青蒿素所做出的重要贡
献。
因为我写过有关伊维菌素的研发故事,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公布之后的几天,我收到了不少询问的微信、电话和邮件,都
是问坎贝尔博士的。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坎贝尔博士不但是我
在默沙东的老前辈,而且也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学长,我挺自
豪的。只有一位女士在电话里弱弱地追问了一句:“那么那个日
本人是干什么的?”我说那位日本老先生就是一个“挖烂污泥的”。
她惊讶地说:“挖烂污泥也能得诺贝尔奖啊!”我们都笑了。虽然是句玩笑话,但是那个排在屠呦呦和坎贝尔之间,中国
人很少提及的大村智先生一辈子收集和研究土壤样品却是一点不
假,他本人在题为“土地的华丽馈赠”的获奖感言中就展示了他收
集土壤样品时的照片。
[12]
其实,大村智不是因研究“烂污泥”而
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人,著名的链霉素发现人、1952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威克斯曼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土壤之人”。 [13]
大村智先生在他的获奖感言中说道:“世界上最重要的、革
命性的、用途广泛的,但相对而言仍旧不出名的药物之一起源于
日本的土壤里,无论从字面上看还是从含义里讲皆是如此。伊维
菌素,一种衍生自单个微生物的药物,每年有超过2.5亿人(是全
日本人口的两倍)可免费获得,就发现于日本的土壤里。它对于
改善数亿男子、妇女和儿童(主要是贫穷和贫困社区)的总体健
康和福利的影响依然是无法比拟的。它打破了许多先入为主的陈
旧观念,尽管这个单一疗法多年来被广泛持续地使用,但耐药性
并未发展。这促使它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清单’,这
是所有基本卫生系统中最重要的药物汇编。一些国际公共卫生专
家也大力推荐,将伊维菌素作为一种简单预防和有效治疗的公共
卫生干预措施,在寄生虫多发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规模地推
广。”
“简而言之,伊维菌素被证明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生物医学发
现之一……对全世界的动物和人类健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有益影
响。”
伊维菌素:匪夷所思的抗寄生虫药
20世纪70年代初,默沙东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与世界各地的研
究机构合作,收集各种土壤样品,从中培养、筛选和寻找抗微生
物的活性物质。结果,在收集到的4万多个土壤样品里,仅在一
个土壤样品的培养和筛选过程中,发现了一类全新的抗寄生虫的
化合物。这个唯一的土壤样品是大村智所在的日本东京北里研究所提供的,它来自静冈地区伊藤市,是川奈海滨的高尔夫球俱乐
部附近收集的单一土壤样品。
这些样品在被送到默沙东实验室之前,大村智在北里研究所
的团队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筛选,并没有发现什么有意义的
东西,所以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在默沙东实验室的一个实验
员将这些土壤样品的培养液用于一些常见的寄生虫时,奇迹出现
了。他发现其中一个样品把所有的寄生虫杀得一干二净,欣喜之
余,他从盛满培养液的烧瓶中取出几滴,放到另一个烧瓶里大量
稀释之后,再用于那些寄生虫,结果还是把所有的寄生虫杀得一
干二净。实验人员将这个已经稀释过的培养液又稀释了一次,得
到的杀虫效果仍旧是一样的。由欣喜转为惊讶,这个实验人员连
续将培养液的稀释过程重复了好几次之后,发现它还是有很强的
杀虫效果。他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筛选的团队,经过几次重复之
后,大家确信无疑,这个培养液里一定存在着一些非常高效的抗
寄生虫的化学物质,他们决定做动物实验,于是故事开头坎贝尔
博士回忆的那一幕出现了。
通过对该菌种的培养、发酵、分离和纯化,默沙东实验室的
研究人员找到了这些化学物质,将它们命名为阿维菌素
(Avermectin)。阿维菌素是一些含糖的大环状内脂类有机化合
物,这个家族的不同成员对不同寄生虫的杀虫效果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化学稳定性也有明显差别,不是很理想。在深入研究的过
程中,默沙东实验室药物化学部的研究人员把阿维菌素家族的一
员——阿维菌素-B1(Avermectin-B1)的一个碳碳双键(C22
=C23 )通过均相催化加氢还原,一步化学反应就做成了一个集中
了阿维菌素家族不同成员优点的新化合物,不但稳定性好,而且
生物利用度也有提高,它就是伊维菌素。
伊维菌素是第一个“体内外杀虫剂”(Endectocide),既能杀
死体内寄生虫,也能杀死体外寄生虫。它的抗寄生虫药性之强实
属罕见,比如,每千克体重0.001毫克的口服剂量就足以杀死狗体
内的幼年心脏蠕虫(Dirolilaria immitis,又名Heart worm),即使对于伊维菌素不太敏感的牛食道口线虫(Oesophagostomum
radiatum)和牛肺蠕虫(Dictyocaulus viviparus),每千克体重
0.05毫克的口服剂量也就够了。相比之下,其他口服药物的用量
在每千克体重40毫克以上。伊维菌素的适用面也很广,能有效地
杀死线蠕虫、跳蚤、虱子等寄生虫,每月一次用药几微克就可以
有效地防止心脏蠕虫对狗的侵害。
寄生虫病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人群里已经很少见了,但在欧美
的畜牧业和宠物业,每年因寄生虫病而造成的商业损失不下40亿
美元。兽用的伊维菌素上市之后,很快成为家畜和宠物抗寄生虫
的理想用药,年销售额接近10亿美元,北里研究所也因此获得了
可观的提成。最初的菌种经发酵后,每立升培养液只能产生大约
9微克的阿维菌素,经过工艺部门的不断筛选和优化,新菌种发
酵后阿维菌素的产量提高了五六个数量级。多年来,只有默沙东
拥有能产生阿维菌素的唯一菌种,直到1999年,意大利的一家实
验室才找到了第二个能产生阿维菌素的菌种,结束了默沙东对它
的垄断。
河盲症:令人生畏的寄生虫病
在人口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各种各样的寄生虫病,如热
带的疟疾、血吸虫病等,依然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在撒哈
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里,有一种令人生畏的寄生虫病,因为多
发于居住在河边的人群,而且会导致患者失明,被称为“河盲
症”(River blindness)。
在水源奇缺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部落民族一般都沿河而
居,以利生息、农耕和放牧。然而,在那一带的河水里繁殖的黑
蝇大多携带着一种被称为“盘尾丝虫”(Onchocerca volvlus)的寄
生虫蚴。在河边作息的人被黑蝇叮咬后,盘尾丝虫蚴便被注入体
内,开始了在人体内的寄生周期。虫蚴在患者的皮下慢慢地长
大,最长的成虫可达两尺。它们聚集于皮下,使患者奇痒无比。
成虫一旦进入患者的眼睛,就会引起角膜的炎症,最终导致失明。在一些发病严重的村落里,5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失明的患者
甚至高达60%。
在研发伊维菌素的过程中,默沙东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注意到
了伊维菌素可以有效地杀死一种与盘尾丝虫很类似的马的寄生
虫,进而敏锐地推断出伊维菌素也许能杀死盘尾丝虫,从而治愈
河盲症。
[14]
他们很快拟订了进一步研究的方案,递交给了当时
主管研发的公司副总裁罗伊·瓦杰洛斯博士。单从账面上看,这又
是一桩赔本的买卖。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集中了世界上最贫困的
国家,生活条件之恶劣、物质资源之匮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研发成本甚高的各大制药公司不可能在那个地区获得任何的利
润。但是,为了坚持以人为本,默沙东公司还是决定做这桩赔本
的买卖。带着探索未知的好奇和征服疾病的强烈欲望,带着救死
扶伤的责任和义务,默沙东实验室的科学家远赴非洲,首先在塞
内加尔开始了小规模的安全评估(Safety assessment,简称安评)
与临床试验,结果非常令人鼓舞,试验也很快扩大到马里、加
纳、利比里亚、乍得等国。伊维菌素对于盘尾丝虫蚴的杀伤力之
强令人匪夷所思:以每公斤体重150微克的剂量,一年口服一次
就足以杀灭所有的盘尾丝虫蚴!
通过了严格的安评之后,默沙东制药决定将兽用伊维菌素用
于河盲症的治疗。但是,由于河盲症仅发生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
非洲国家和少数拉美国家,美国没有病例,所以河盲症不是FDA
的注册疾病,将伊维菌素用于河盲症根本就无法在美国申请报
批。
[15]
好在旅居法国的非洲移民中有少数河盲症的病例,使它
成为法国医药管理部门的注册疾病,于是默沙东将人用伊维菌素
(商品名改为Mectizan)在法国申报,并获得批准。
慷慨解囊:史无前例的医药捐赠
新的问题又来了:如何才能将伊维菌素送到当地居民的手
里?那些国家没有健全的医保和公共卫生系统,很多地方连公路都没有,有些偏僻的村寨甚至连越野车也开不进去。
尽管每年只需口服一次,但谁来为这些伊维菌素的生产和销
售买单?不管药价定得多低,那近2000万河盲症患者和8000万受
河盲症威胁的非洲老百姓都不可能买得起。而免费捐赠又有悖于
必须依靠利润才能有巨额资金投入新药研发的现代制药工业模
式。面对这个两难的选择,从主管研发的副总裁晋升为默沙东首
席执行官的瓦杰洛斯博士说服了董事会,毅然决定向全球所有被
盘尾丝虫感染和受到感染威胁的人群无限期无偿提供伊维菌素,直至河盲症这一公共健康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默沙东的这一决定,他们认为上市的制
药公司应该为它的持股人提供最高的红利,而不应该牺牲持股人
的利益来参与慈善事业,因为那是慈善机构该做的事。然而,这
一举动充分体现了默沙东一以贯之的“以人为本”和“为社会提供更
好的产品和服务”的宗旨,赢得了社会的尊重,极大地提高了默
沙东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献身精神,也使默沙东成为有志于医
药工业的年轻人心目中理想公司的首选,被美国《财富》杂志连
续7年评为“全球最令人敬佩的公司”。
现代制药是一项尖端科技产业,涉及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
优秀科技人才的聚集大大提高了默沙东的科研水平,确立了默沙
东在制药界的领先地位。长期以来,默沙东实验室在基础医药
学、化学、生物技术等各个生命科学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
性的进展,一直被学术界的广大同仁所推崇,享有很高的声誉。
每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都要发表相当数量的高水平
学术论文,足以跟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所比肩,他们经常被邀请
去大学、研究所和各种学术会议做演讲。反过来,默沙东实验室
每年也邀请许多大学和研究所的著名学科带头人,以及学术界年
轻的后起之秀来做演讲,进行学术交流。许多原本看好学术机构
的科研人才纷纷加入默沙东实验室,年轻的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
更是以加入默沙东实验室为荣,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业界的同行不无妒忌地戏称默沙东实验室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生命学科
博士毕业生的首轮“选秀权”。
以人为本的精神吸引了优秀的人才,优秀的人才创造出了更
优秀的科技。从长远看,默沙东的捐赠决定还是为它的持股人带
来了更多的利益。
功不可没:指日可待的河盲绝灭
制药是为了救死扶伤,祛病消灾,在这个层面上,伊维菌素
对提高和改善整个人类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条件的贡献是无法用金
钱来衡量的。从1988年开始,默沙东与卡特基金会合作,在众多
志愿者的参与下,持续向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各个非洲国家分
发伊维菌素。随后,伊维菌素的无偿捐赠又扩展到拉丁美洲的安
提瓜、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等国。鉴于在
非洲国家和也门丝虫病和河盲症并存,1998年默沙东将伊维菌素
捐赠项目扩展至丝虫病的治疗。
截至2012年,默沙东已为非洲、拉丁美洲及也门的11.7万个
群体捐赠了价值51亿美元的伊维菌素片,并为伊维菌素捐赠项目
提供了约4500万美元的直接资金支持。在拉丁美洲的6个流行国
家中有4个国家的河盲症传播已被遏制,在5个非洲国家的9个地
区的传播也同样被遏制,没有新病例出现。
默沙东公司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福维泽说:“25年后,伊
维菌素捐赠项目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在全世界逐步实现消除河
盲症这一长期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带来改变,这是振奋人心
的。我们惊叹于这一合作联盟在保护后代免受河盲症病痛中的突
出表现,河盲症会给患病者及其家人、医疗系统和当地经济带来
灾难性的后果。捐赠项目的成功表明:通过合作,我们可以成功
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健康问题,即使是容易被忽略的地区和容易
被忽略的疾病。”独特的公私团体合作使伊维菌素捐赠项目的实施成为可能。
这一合作的参与者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全球卫生工作
组、非洲盘尾丝虫病控制项目(APOC)、美洲盘尾丝虫病根除
项目(OEPA),以及流行国家的卫生部门、非政府发展组织和
当地团体。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也表示:“默沙东的伊维菌素捐赠项目
史无前例,25年来在为河盲症患者减轻病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之前我们对解决非洲河盲症的预期仅是控制,但目前一些非
洲国家在彻底消灭河盲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西半球,卡特
中心及其合作伙伴几乎将河盲症彻底根除。因为默沙东的贡献、病症流行国家的支持以及强大的合作,我们可以预见一个没有河
盲症的世界。”
每年的10月11日是世界视力日,启动伊维菌素捐赠项目30年
后的今天,默沙东与合作伙伴共同庆祝了在消灭河盲症进程中取
得的重大进展。河盲症是世界范围内导致可预防性失明的主要原
因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伊维菌素的无偿捐赠有希望使河
盲症在2020年前后从地球上绝迹,可以说是继牛痘灭绝天花之
后,人类医药健康史上又一个伟大的成就。喜欢本书吗?更多免
费书下载请***:YabookA,或搜索“雅书”。
2011年5月初稿于新泽西
2017年8月修改稿于新泽西第四章 遭遇“黑天鹅”的有准备之人
保列治和保发止的发现
原始制药(确切地说应该是找药)都是没有分子靶标的。从
神农尝百草开始,一直到生命科学发展到分子水平之前,找药都
是直接针对疾病症状的。这样做,成功的几率很低,因为只能做
表观的筛选而无法进行系统性的优化,基本就是碰运气。更重要
的是,在没有动物疾病模型的情况下,直接在自己或患者身上试
药是非常危险的,传说中的神农氏就是因为误食“断肠草”而客死
他乡的。
不期而终的荷尔蒙研究
现代分子生物医学的创立,使我们在近几十年里对许多疾病
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人体胆固醇的调控,包括胆固醇的
生物合成和转移,摄入胆固醇的吸收和代谢,以及胆固醇与心脏
病之间的联系,等等。基于这些基础研究的结果,以羟甲基戊二
酰辅酶A还原酶(HMG-CoA reductase)为药靶,默沙东等几大制
药公司先后研发出了历史上销售量最大的“他汀”(Statin)类药
物,如舒降之,大大降低了冠心病患者心梗的风险。
[16]
可是,在很多情况下,在早期研究中被看好的分子药靶要么不能被验
证,要么与毒性相关,甚至可能因为没有合适的市场,而得不到
进一步研发。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默沙东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就开始了
对男性荷尔蒙的研究,希望能找到治疗青春期粉刺的新药。青春
期是性荷尔蒙活动的旺盛期,随之出现的青春期粉刺多半与男性
荷尔蒙的活动有关系。当时主要有两个已知的甾体类雄性激素(Steroid hormones):睾丸酮(Testosterone)和作用更强的二氢
睾丸酮(Dihydrotestosterone, DHT),默沙东的研究团队认
为,如果抑制将睾丸酮转化为二氢睾丸酮的5-α还原酶,应该可以
降低体内男性荷尔蒙的活动,也许可以抑制粉刺的生长。
基于这样一个假设,默沙东实验室组成了多学科的项目团
队,一方面深入研究青春期粉刺与男性荷尔蒙活动的关系,试图
从机理上验证该项目的可行性,另一方面积极寻找高活性、高选
择性的5-α还原酶的抑制剂。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合成了相当数
目的新型抑制剂,同时也建立了一整套生物测试方法,用于筛选
和评估这些新型的抑制剂。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积累了大量的有
关二氢睾丸酮和5-α还原酶的数据和知识。制药项目的进展,说到
底就是有关该疾病与分子靶标的知识积累。随着知识的不断积
累,项目团队才有可能设计出理想的化合物。
但是,随着项目的进展,公司意识到,给青少年使用甾体类
激素药物是难以被社会接受的,即使研发成功,市场营销的困难
也将会很大,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终止了5-α还原酶抑制剂的
研究项目。
多米尼加的古怪病例
几乎就在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发生
了一件听上去毫不相干的事情。一个来自偏远部落的小女孩因病
被送进医院做腹腔手术,结果医生发现“她”实际是个男孩!谁也
没想到,若干年之后,这个意外发现给5-α还原酶抑制剂的研究项
目带来了转机,并最终促成了不止一种,而是两种新药的发现。
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和西南医学中心的科学家们首先注意到了
这个不寻常的病例,他们深入丛林,对那个偏远部落的人群进行
了几年的跟踪研究,发现该地区的许多男性都有类似的经历。他
们出生时外生殖器呈雌性,所以被当成女孩来抚养。但到了发育
期间,他们的雄性特征开始显现,并长出男性外生殖器,成为男人。1974年,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教授朱丽安·英珀拉托-麦金利在
一个讨论新生儿生理缺陷的学术会议上首次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
果。
他们发现,这些所谓的“假双性儿
童”(Pseudohermaphrodites)其实都是男孩,只是在出生时,他
们的性腺(Gonads)尚未长成,所以外生殖器呈雌性,被误认为
是女孩。青春期时,他们的性腺开始发育,大多能长出男性生殖
器,成为正常男人。这些在发育期“变性”的男人进入老年以后不
会脱发变成秃头(男性型脱发[Male pattern baldness,简称
MPB]),他们的前列腺相对都很小,而且老年时也不会增生。
这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丛林深处的部落,与外界的接触很有
限,所以他们的遗传基因也与外界相对隔绝。假双性儿童的现
象,很有可能是某种遗传共性的表象。果不其然,进一步的遗传
学研究结果显示,这些特殊的多米尼加部落男性体内二氢睾丸酮
的含量大大低于正常男性的水平,因为这些部落的大多数男性有
一个共同的遗传缺陷:他们都缺少将睾丸酮转化为二氢睾丸酮的
5-α还原酶。
掠过天际的黑天鹅
药物研发与所有科学研究一样,是在探索未知的世界。
但是“未知”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另一类是“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这
话听起来有点绕,下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
某地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煤炭,于是有人就组织了一支勘探
队到附近别的山洞里也去找煤炭。是不是能找到煤炭?没有人知
道,这就是已知的未知。但是他们找来找去,没有找到煤炭,却
在另一个山洞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古代的墓葬,有大量的陪葬
品。山洞里的古代墓葬在被发现之前就是未知的未知,所以不会有人专门去找。现在有人发现了,那就会有更多的探险队去寻
宝,这时的古代墓葬就不再是未知的未知了。在这个例子里,如
果把煤炭和古代墓葬换过来,先发现的是古代墓葬,在寻找更多
古代墓葬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煤炭,那么古代墓葬就是已知的未
知,而煤炭则成了未知的未知,就看你的初始条件是什么。
已知的未知有很多,严格来讲,每一个科学家的工作都是在
试图发现某一个或几个已知的未知。所有立项的新药研发也是一
样,都是在寻找已知的未知,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要找什么,有
靶点,有目标,不管最后找到找不到,都属于已知的未知,这里
包括研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多种事件,比如心律紊乱、肝脏代谢
酶受阻、肾功能受损等,尽管这些结果都无法预见。因为我们事
先知道这些情况有存在的可能性,并且一定会刻意去筛查,如果
它们一旦发生了,项目团队也都有应对的策略,所以它们都属于
已知的未知,只是出现的几率有大有小而已。
那么未知的未知有多少呢?回答是“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就
不再是未知的未知,而是已知的未知了。著名作家纳西姆·塔力布
在他的畅销书《黑天鹅》里把这种未知的未知比作“黑天鹅”,使
它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术语。
在18世纪欧洲人发现澳洲大陆之前,他们见过的所有天鹅都
是白色的,所以在当时欧洲人的眼中,天鹅就只能是白色的。直
到欧洲人发现澳洲,在第一次看到当地的黑天鹅之后才认识
到,“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一般性结论是错误的。仅仅一只
黑天鹅的出现,就颠覆了前人从无数次对白天鹅的观察中所归纳
出的一般性结论,引起了人们对认知的反思——以往认为对的不
等于以后总是对的。
这些黑天鹅是不可预见的,它们一旦掠过天际,便会影响巨
大。
慧眼识珠的有准备之人在不断探索未知的科学领域里,遭遇黑天鹅其实并不是太
难,难的是认识黑天鹅。
牛顿是第一个被树上掉下来的果实砸到脑袋的人吗?从概率
上讲几乎不可能是,但在牛顿之前,没有人认识到这是一只“黑
天鹅”,它揭示了一个很重要、但在当时不为人知的存在。正在
研究运动学的牛顿提出了“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升,而是往地上
掉”这一关键问题,认为有一种未知的“力”在起作用,于是我们有
了划时代的万有引力定律。弗莱明爵士是第一个注意到青霉菌落
的周围有个亮环的人吗?从记载来看也不一定是,但在弗莱明之
前,没有人认识到这也是一只“黑天鹅”,它也揭示了一个很重
要、但在当时不为人知的存在。正在研究细菌学的弗莱明意识到
了这些亮环应该是无菌的区域——“这些青霉菌落里一定有些什
么奇妙的东西”,并且花了大量时间去寻找到这个“奇妙的东西”,于是我们有了突破性的抗菌新药——青霉素。
1948年,美国佐治亚医学院药理学家雷蒙德·P.安奎斯特
(Raymond P. Ahlquist)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没想到成文
投稿之后却被一家著名的科学杂志拒绝了,他不得不通过熟
人“走后门”才在《美国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他在该文中指出:
如果有两种不同的肾上腺素受体(α-受体和β-受体)存在,那么
肾上腺素与去肾上腺素之间相互矛盾的生物效应就很容易解释
了,因为它们调控不同的生物回路。安奎斯特的这个观点在当时
实在是太颠覆了,就好像是在说“天边飞过的那只黑鸟也许是一
只天鹅”。那些看惯了“白天鹅”的同行们当然都认为他看花了眼,所以发表之后也没人关注,以至于整整十年之后才有识货的学者
站出来说:我认为那真的就是一只黑天鹅,值得我们去找一找。
他就是英国著名药理学家詹姆斯·W.布莱克(James W. Black)爵
士。
为了找到这只黑天鹅,布莱克辞去教授职位,加入英国ICI制
药公司,并成功地说服了公司领导,率队立项研发选择性的肾上
腺素β-受体拮抗剂,这在当时还不存在。这时的“黑天鹅”其实已经不黑了,因为有了安奎斯特的大胆假设,它经历了从未知的未
知到已知的未知的关键性转变。十年求索,几度沉浮,布莱克领
导的研发团队终于找到了那只最先被安奎斯特根据一鳞半爪的实
验数据推测出来的“黑天鹅”,成功地研发出了一类创新药物β-受
体阻断剂(β-Blocker)。这一巨大成功不但使蛋白质受体亚型成
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事实,而且布莱克本人也修成正果,荣获
198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安奎斯特呢?好在还是有人想到
了他。1976年,他与布莱克共享了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17]。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头顶的天空上不断飞过的各种东
西里边,时不时就会有无人知晓的、真正的“黑天鹅”。其中有一
些招摇过市,能立刻引起轰动,但还有很多悄然掠过,只给我们
留下短暂的一瞥。
康奈尔大学和西南医学中心对加勒比海岛部落民“假双性
人”的遗传学研究结果是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每个新药研发人
员都看得到,好比一只“黑天鹅”从闹市的上空飞过。但是,在这
个“闹市”(新药研发圈)里看热闹的人群中,有这么两位识货的
行家:一位是当时默沙东的首席科学家瓦杰洛斯博士,另一位是
曾经领导默沙东5-α还原酶抑制剂项目的科学家格伦·亚斯(Glen
Arth)博士。他们俩手里拿着刚打印出来的同一篇文献,冲出办
公室,相遇在楼道里……
良性增生的前列腺
这篇有点旁门左道的遗传学研究报道,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只是科学的花边新闻,但是不久前认真研究过5-α还原酶的默沙东
的科学家们却敏锐地意识到:5-α还原酶的抑制剂也可以降低正常
人体内二氢睾丸酮的含量,也应该可以用来防止和治疗老年性的
良性前列腺增生(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简称BPH)。用
甾体类药物给青少年治疗青春期粉刺也许没有什么市场,但用于
老年人的前列腺增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5-α还原酶抑制剂的目标不应该是青年人的粉刺,而应该是老年人的前列腺。
前列腺是男性特有的性腺器官,具有内、外双重分泌功能的
性分泌腺。作为外分泌腺,前列腺每天分泌约2毫升前列腺液,是构成精液的主要成分;作为内分泌腺,前列腺分泌的激素称
为“前列腺素”。前列腺位于膀胱底部,尿道从它的中间穿过。进
入更年期后的男性,由于性激素代谢的变化,会因为不同程度腺
体和(或)纤维、肌肉组织增生而造成前列腺体积增大。增生的
前列腺挤压尿道,导致一系列排尿障碍症状,如尿频尿急、夜尿
增多、尿流细弱、尿不尽等。这些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许多严重的并发症(如急性尿潴留、结
石、肾积水和肾功能不全等),甚至会危及患者的生命。良性的
增生大多发展缓慢,往往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排尿障碍症状也
被认为是正常的衰老过程。
据统计,全球约有1.05亿人受到影响。
[18]
在50岁以上的男
性人群里,显现出不同程度的良性前列腺增生临床症状的人数约
占50%(每两人中就有一个,还不包括已有增生但尚未出现临床
症状的人群),[19]
而在80岁以上的男性人群里,有临床症状的
前列腺增生患者高达90%。
[20]
毫不夸张地讲,每个男人上了年
纪,他的前列腺多多少少是要增生的。现代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所以受前列腺增生困扰的老人也就越来越多。当时没有有效的药
物能防治前列腺增生,重症患者必须动手术切除增生的部分,疏
通尿路,所以新型有效药物的潜在市场应该是相当大的。
保列治与保发止
将靶标锁定在前列腺之后,默沙东重新启动了5-α还原酶抑制
剂的研究项目。又经历了十几个冬夏之后,默沙东实验室的科研
团队终于将保列治(Proscar,药名为非那雄胺[Finasteride])申报FDA批准,并于1992年投放市场,成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
的第一个口服药物。在临床试验过程中,保列治显示的功效比预
计的要好很多,它不但阻止了前列腺的增生,而且还能使已经肥
大的前列腺缩小20%~25%,大大减少了手术治疗的必要性。
泌尿科的医生一开始不以为然,甚至不太情愿开处方让病人
服用保列治,他们的理由是手术治疗见效快,而服用保列治则需
要时日;另一方面,他们不想看到手术病人的快速减少。为了打
开保列治的市场,默沙东决定直接向最终的消费者——患者——
做广告,让他们了解手术治疗以外的选择和药物治疗的优缺点,成为最终的受益者。处方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大规模广告宣传在
美国制药界是首创,颇有争议。舆论认为,制药公司的钱应该花
在新药研发上,而不应该花在市场营销上。但事实证明,让消费
者了解新药的功效也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保列治的上市没有引起
爆发性的轰动,但还是逐渐被患者和医务人员所接受。口服保列
治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其处方销售也稳步上升。
保列治治疗前列腺增生的成功使默沙东的科研人员有机会进
一步研究5-α还原酶与男性型脱发之间的联系。男性型脱发是因为
头皮中的双氢睾酮含量增加,使得毛囊逐渐萎缩,头发变细,头
发数量减少。经过几年资源的大量投入之后,第二个5-α还原酶抑
制剂药物保发止(Propecia)在1997年上市了。保发止和保列治
的有效成分是相同的,只是剂型和剂量不同。在为期5年的临床
试验里,已开始部分脱发的男性服用保发止后都没有进一步脱
发,其中约66%的患者还长出了一些新的头发,而服用安慰剂的
患者却继续脱发。独立的照片分析结果也表明,服用保发止的患
者中有48%头发明显增加了,另外42%则没有继续脱发,效果是
显著的。
中国目前大约有1.3亿的男性型脱发患者,但是去医院接受正
规治疗的还不足三成。很多患者在脱发初期用生姜擦头皮、防脱
洗发水等错误方法,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通过服用保发止可降
低体内双氢睾酮浓度,服药后3个月脱发开始减缓,6~9个月新头发开始生长,1~2年可达最好疗效。当然,任何药物都有副作
用。5-α还原酶抑制剂的主要副作用是少数服药者会出现性功能减
弱,个别病人甚至会出现阳痿。对于前列腺增生的老人,这个风
险也许已经不再重要,但对于脱发的青壮年,却需要认真权衡其
中的利弊。
医学界对那些多米尼加部落人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那里的
男性除了不脱发和没有前列腺增生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前
列腺癌症的患者。为此,默沙东实验室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合
作,开展了大规模的长期临床试验,研究保列治对前列腺癌的防
治作用,目前尚无定论。
机遇垂青于有准备之人
保列治和保发止的发现又一次印证了著名科学家路易·巴斯德
的名言:“机遇垂青于有准备之人。”20世纪60年代默沙东实验室
对男性荷尔蒙和5-α还原酶的研究,为日后保列治的研发打下了很
好的基础,不但积累了合成这类化合物的经验,建立了有效的酶
活性生物测试方法,更重要的是,积累了有关睾丸酮、二氢睾丸
酮和5-α还原酶的知识,为寻找这个代谢途径里的相关药靶做好了
准备,并且密切关注这一领域里的科研新动向。所以,到了20世
纪70年代中后期,有关多米尼加“变性人”的报道及其跟踪研究立
刻引起了默沙东科研人员的注意,他们抓住了这个貌似毫不相
关、很容易被忽略的机会。
中国目前的基础生物医学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人力和物力
的总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而通过独立自主的基
础研究来发现和验证新的药靶投入高,周期长,很难在短时期内
成为主流方向。但是,中国的医药界精英应该注意积累各种常见
病、多发病的病理知识,密切关注全球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的新动
向和新发现,做有准备之人。
没人能准确预测下一只“黑天鹅”会在何时何地出现,但发现和捕捉到下一只“黑天鹅”的人一定是有准备之人。喜欢本书吗?
更多免费书下载请***:YabookA,或搜索“雅书”。
你准备好了吗?
2013年1月初稿于新泽西
2017年10月修改稿于新泽西第五章 从后继专利药到更优专利药
降压药依那普利的成功逆袭
新药研发的竞争是白热化的,原因之一是,已知可用药的生
物靶标(Drugable targets)是有限的,一经临床前的药理验证
(Pharmacological validation),或是更进一步的临床验证
(Clinical validation),各大公司的研发资源就都集中在了这些
有限的药靶上了。成功希望越大、市场前景越看好的药靶,竞争
就会越激烈。就拿二肽酰肽酶-4抑制剂的研发来看,默沙东原创
的西格列汀(Sitagliptin)
[21]
成功之时,已有十多家药厂的格列
汀类的候选药物先后进入了临床试验,力争在后继专利药中取得
领先地位。更为理想的当然是能在疗效、安全性或是依从性等方
面超过已经上市的专利药,后来居上成为更优专利药。
对跨国大药厂来说,创新药是首选,更优药其次,后继药则
是不得已的选择。创新药物一般可占据市场份额的60%~80%;
更优药如果在疗效、安全性或依从性方面确有优势,一般能够后
来居上,占据市场的主要份额(>50%)。但是疗效和安全性大
致相仿的后继药,基本上只能有10%~20%的市场份额,所以在
大量的资源投入之后,如果不能争其先,就必须求其上。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简称ACE)抑制剂的研发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实例。
关于血压的是非曲折
在1628年出版的《心脏与血液的运动》一书中,英国医生威
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总结了前人和他自己的研
究工作,提出了相对完整的血液循环理论,从此人类对于“心血管系统”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过了一百多年,英国牧师斯
蒂芬·海尔斯(Stephen Hales)于1733年首次公布了血压的测量方
法,但是血压测量在临床医学上的真正普及,则一直要到1896年
基于袖带的血压计发明之后,从此操作变得十分简便。
进入20世纪,随着血压测量数据的累积,将血压升高作为疾
病的描述也日益增多。在高血压患者中,绝大多数是原发性的,约占95%,发病的原因还不清楚,但往往与家族病史相关,可能
是环境和遗传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928年,美国梅奥诊所的医
生描述了一种特殊的高血压,伴有严重的视网膜病症,但肾功能
正常。因为患者通常在一年内因中风、心力衰竭或肾功能衰竭而
导致死亡,所以它被称为“恶性高血压”(Malignant
hypertension)。
虽然严重或恶性高血压对健康的威胁很早就得到了充分的认
识,但所谓的“良性”血压升高的风险及其治疗一直是有争议的。
早在1931年,利物浦大学医学教授约翰·海(John Hay)就认为,高血压患者面临的最大风险就在于我们发现了它,因为肯定会有
一些傻子去设法降低它。美国著名的心脏病学家保罗·D.怀特
(Paul D. White)在1937年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虽然
我们确信自己能够控制,但高血压也许是一个重要的补偿机制,不应该被随意扰动。”查尔斯·弗里德伯格(Charles Friedberg)在
1949年的经典教科书《心脏疾病》中指出,“患有‘轻度良性’高血
压的人不需要治疗”,而当时对“轻度良性”高血压的定义是血压为
210100 mmHg。
从20世纪50年代起,心肺医学主流意见的大潮发生了转向,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良性”的原发性高血压并不是无害
的。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析报告和跟踪研
究(例如1974年美国国立卫生院心肺研究所发表的《弗雷明汉心
脏研究》
[22]),积累的证据表明,“良性”高血压也会导致心血
管疾病和增加死亡的风险,在普遍的高血压患者群中,这些风险
随着血压的升高而逐渐增加。与此同时,基础医学对于血压调控的机理研究也逐渐深入到
了分子水平,使得小分子化学介入成为可能。
血压调控与化学介入
血管紧张肽原酶(Renin)是人类最早发现的蛋白酶,距今
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一百多年里,由血管紧张肽原酶和
血管紧张肽所构成的生物调控体系(Renin-angiotensin system,简
称RAS或RAAS
[23])一直是基础医学和临床研究的热门领域,因为RAAS对人体的体液和电解质平衡以及血压的调控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简单地讲,当人体内血量降低(失血)时,肾脏就会
释放血管紧张肽原酶。血管紧张肽原酶将储存于肝脏内的血管紧
张肽原(Angiotensinogen)通过降解转变为血管紧张肽-
Ⅰ(Angiotensin-I),新产生的血管紧张肽-I在肺循环
(Pulmonary circulation)过程中被血管紧张肽转换酶(ACE)进
一步转换为血管紧张肽-Ⅱ。血管紧张肽-Ⅱ作为激动剂
(Agonist)将其受体(Angiotensin-Ⅱ receptor)激活,从而引起
下游一系列相应的生理变化,最终导致血管壁紧缩,血压升高。
这是人体自我保护、保障器官供血的重要机制。
与此相反,血管舒缓激肽(Bradykinin)则通过另一类受体
(Bradykinin receptor)而引起血管舒张,降低血压,达到平衡,以避免因血压升高而可能导致的一系列不良反应。对于高血压患
者来说,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吸烟、酗酒、肥胖、精神压力等,他们的RAAS调控体系的平衡点发生了偏移,血压被维持在较高
的状态下,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增加了心梗、脑梗等突发性病变
的风险。
长期以来,各大药厂的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寻找能干预
RAAS调控体系的小分子,通过阻断或促进其中的某个环节而降
低血压,建立新的调控平衡。值得注意的是,血管舒缓激肽与血
管紧张肽一样,主要也是在肺循环的过程中被血管紧张肽转换酶ACE降解的,由此不难得出结论,血管紧张肽转换酶对血压调控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血管紧张肽转换酶抑制剂(ACE
inhibitor)就是20世纪80年代从RAAS体系中研发出来的第一类高
效降压药——普利类降压药。
[24]
1981年4月,施贵宝制药在各大药厂的ACE抑制剂项目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将第一个普利类降压药卡托普利(Captopril,商
用名Capoten)推上了市场,开启了RAAS体系药物研发的新时
代。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又有十多个普利类的降压药陆续上市,可见医药界对ACE抑制剂研发的投入之多,竞争之激烈。
卡托普利与药物设计
卡托普利的成功给药物化学带来了实质性的进步,以化学结
构为基础的新药设计(Structure-based drug design)从此进入主
流,成为应用最普遍的药物化学方法之一。
20世纪70年代初,巴西科学家从美洲洞蛇(Bothrops
jararaca)的毒液中发现了一组多肽,能够增强血管舒缓激肽的功
效,被命名为“血管舒缓激肽增强因子”(Bradykinin potentiating
factor,简称BPF)。剑桥大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BPF能抑制从血
管紧张肽-Ⅰ到血管紧张肽-Ⅱ的转化,正是血管紧张肽转换酶的
抑制剂。这一重要的发现,给原来无从下手的药物化学家们提供
了一个出发点。但是如何把这些因为药代动力学性质不佳而不能
开发成口服药物的多肽分子转化为可开发的化学小分子,在当时
是一个十分前沿的课题。
施贵宝制药研究团队以这些天然的多肽类ACE抑制剂为起
点,采用当时很先进的定位突变(Site-directed mutagenesis)生物
技术
[25]
,仔细研究了BPF的构效关系(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简称SAR)。他们发现这些多肽C末端的脯氨酸残基
对ACE的抑制活性非常重要,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药效基团”(Pharmacophore)
[26]。以这个脯氨酸残基为核心,施贵宝
制药团队合成了2000多个衍生物,通过生物测试,他们发现在脯
氨酸附近引入巯基(Thiol group,或-SH)能进一步提高化合物对
ACE的抑制活性。在巯基和脯氨酸残基这两个结构单元的基础
上,他们找到了高效率的ACE抑制剂,成功地设计出了卡托普利
(见图5-1)。
图5-1 卡托普利
在整个研发过程中,施贵宝的团队把化合物结构单元放在首
位,通过对药效基团的定位(Pharmacophore mapping)建立构效
关系,逐步向高效率的ACE抑制剂靠拢,直至最后成功地设计出
卡托普利。这是第一个以化学结构为基础的新药设计的成功例
子,从那以后,这种先进的思想方法得到了广大药物化学家的接
受,成为现代药物化学的主流。
伊纳普利与更优药物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关键性的巯基给卡托普利带来的对血管紧张肽转化酶的高效抑制,使施贵宝占得了开发普利类药物
的先机;但是,巯基也给卡托普利带来了与其相关的副作用,给
其他药厂后继药的研发留下了提高的空间。
面对施贵宝在ACE抑制剂研发方面的领先局面,默沙东实验
室的研究人员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卡托普利的研发,尤其是其临床
试验的结果。含巯基的卡托普利化学结构一经发表,默沙东实验
室的课题组立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基于从其他项目得来的
类似经验,大家认为巯基很有可能造成三种类型的副作用:白细
胞降低、皮疹和影响味觉。于是,默沙东的课题组把设计不含巯
基的ACE抑制剂作为新的目标,力争研发出同样高效,但更安
全、副作用更小的普利类新药,成为更优专利药。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施贵宝的ACE抑制剂的构效关系已经
显示,巯基是卡托普利与ACE结合的主要官能团,置换巯基会大
大减少该化合物与ACE的结合能,丧失抑制功效。反应过渡态机
理研究结果表明,ACE是一种金属蛋白酶(Metalloprotease),锌离子参与了它所催化的降解反应,而巯基则是已知的很强的锌
离子键合基团,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有效地抑制了ACE的催化活
性。那么,有没有不含硫的锌离子键合基团呢?答案是肯定的。
可是将这些已知的锌离子键合基团引进分子之后,对ACE的抑制
活性不够强,效果不理想。
就在默沙东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积极寻找其他锌离子键合基团
时,卡托普利的临床研究报告公布了。卡托普利的降压效果很
好,但在高剂量时果然出现了一些副作用。部分高血压患者服用
卡托普利后会出现白细胞降低和皮疹,还有一部分患者的味觉受
到影响,严重时甚至会暂时失去味觉。这些副作用决定了卡托普
利只能服用较低的剂量。另外,卡托普利的药代动力学参数也不
够理想,尤其是半衰期较短,患者每日必须服药2~3次,给长期
服用造成相当大的不便。这些预料之中的结果增强了默沙东管理
层和研究团队的信心,他们投入了更多的资源,终于在一年多的
时间里,找到了一种新型的组合。在先导化合物的优化过程中,默沙东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发
现,虽然用羧基直接取代巯基的效果不佳,但羧基和苯乙基的组
合效果却很好,这就是后来的“依那普利拉”(Enalaprilat,见图5-
2)。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依那普利拉对ACE的抑制活性(Ki为
0.2 nmolL)虽好,但口服生物利用度(Oral bioavailability,或
F%)很低,半衰期仅为1.3小时。为了赶超卡托普利,默沙东的
团队应用了“前体药”(Pro-drug)
[27]
的概念,将依那普利拉的羧
基转化为乙酯,成功地研发出了第二个在美国被批准使用的ACE
抑制剂——依那普利(Enalapril,商用名Vasotec,见图5-2)。
图5-2 依那普利拉(R=H),依那普利(R=Et)
依那普利本身的活性并不高,必须经肝脏的酯酶水解后才能
产生高活性的二羧酸依那普利,即依那普利拉。依那普利口服后
吸收迅速,生物利用度约60%(不受食物影响),虽然依那普利
在1小时内达到血浆峰值浓度,但依那普利拉则需3~4小时才能
达到血浆峰值浓度。依那普利拉与ACE的结合非常紧密,因此血
浆半衰期约为11小时,非常适合每日一次的服药间隔。除了普利
类药物共有的一些轻微的副作用(如干咳)外,依那普利即使在
高剂量服用时也没有发现白细胞降低、皮疹和丧失味觉这些卡托
普利特有的副作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由于上述优点,依那普利在1985年12月被批准上市以后,销
售额迅速而又稳步地上升。尽管比卡托普利晚了4年半,但它很
快就在全球范围内超越卡托普利,成为ACE抑制剂降压药的首
选。到了1988年,依那普利已经成为默沙东制药史上第一个年销
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大药。
从依那普利的成功逆袭可以看出,要在竞争白热化的新药研
发领域取得成功,除了要有敏锐前瞻的眼光,能够从基础医学研
究的最新进展中发现可以用药的靶标外,还必须知己知彼,善于
从竞争者已知的临床试验新药,或者已经批准上市的专利药里找
到提高和优化的空间,争取后来居上。
依那普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不是完美的,高血压的治
疗并没有就此止步不前。前面提到,维持一定的血压是至关重要
的,所以在RAAS调控体系中,有许多反馈的回路和补偿机制。
仅靠抑制ACE的活性,仍然不能有效地治疗不同类型的严重高血
压患者。2000年,全球范围内仍有将近10亿人患有高血压,其中
发达国家约占3.3亿,发展中国家约占6.4亿。在成年人中,高血
压患者的比例更是高达26%(每4人中就有1个患者),其中男性
的比例略高于女性。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的成年
人中高血压患者大约有7500万,占32%。2014年,美国以高血压
为主要原因的死亡人数超过41万,每天就有大约1000人死亡。
2004年10月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现状》
[28]
调查结果显
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18.8%,估计全国患病
人数超过1.6亿。虽然患病率略低于发达国家,但上升趋势明显,与1991年相比,患病率上升了31%,患病人数增加约7000多万
人。到了2011年,《北京健康白皮书》显示,北京市18~79岁的
常住居民中,高血压患病率为33.8%,其中18~30岁男性为18.4%
(每5人中有1人),30~40岁男性为31.1%(每3人中有1人),40至50岁男性已接近50%(每2人中就有1人),40~50岁的女性
患者亦高达30%。因此提高对高血压病的认识,对早期预防和及时治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一项大规模的荟萃分析中,血压升高与心血管事件风险之
间清楚地显示了持续的、一致的和独立的相关性。
[29]
该分析包
括了100万名40~89岁、无心血管病史的高血压患者,平均数据
跨度达12.7年(共1270万人年),其中大约有5.6万例死于心血管
性疾病(1.2万例中风、3.4万例缺血性心脏病和1万例其他心血管
病),其他死亡人数为6.6万人。根据此项分析结果,美国高血压
预防、检测、评估和治疗联合委员会在2003年重新定义了高血压
的临床诊断标准。2017年,美国心脏协会再一次降低了(门诊测
量)高血压的指标。根据最近公布的指南,正常血压的标准不
变,收缩压小于120 mmHg,舒张压小于80 mmHg。成人警戒区
被称为“血压升高”,最高收缩压被削减至120~129mmHg,而收
缩压在130~139mmHg之间,或舒张压在80~90mmHg之间为“1
级高血压”,达到或超过14090mmHg为2级高血压。
只要还有高血压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降压药的研发就不
会停止。在继续深入研究RAAS血压调控体系的过程中,默沙东
又相继把新一代的降压药科素亚(Cozaar)与海捷亚(Hyzaar)
推上了市场。
似曾相识的新药设计
血管紧张肽转换酶抑制剂的成功,说明了血管紧张肽-Ⅱ确实
是引起血压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可以激活其受体,从而引起
一系列相应的生理反应,最终导致血压升高。因此人们很自然地
想到了直接用血管紧张肽-Ⅱ受体的拮抗剂(A-Ⅱreceptor
antagonist)来抑制该受体的活性,应该可以起到降低血压的作
用。在RAAS血压调控体系中,血管紧张肽-Ⅱ受体是依那普利下
游的靶标,降压的机制更直接,效果也应该更显著。
虽然选择性的血管紧张肽-Ⅱ受体拮抗剂的研发在20世纪70年
代末被普遍看好,但是具体立项却有相当大的困难。当时的情况非常类似于在开发卡托普利时发现“血管舒缓激肽增强因子”的阶
段,只有一个被称为“肌丙抗增压素”(Saralasin)的多肽对血管
紧张肽-Ⅱ受体有一定的拮抗作用,没有适合的小分子作为药物化
学的先导化合物。直到1982年,日本武田制药发表了两项专利,揭示了两种非肽类小分子血管紧张肽-Ⅱ受体拮抗剂,但是活性很
弱。
杜邦制药的科研人员对血管紧张肽-Ⅱ进行了仔细的构象分
析,他们通过二维核磁共振构建了分子的三维构象,再把武田制
药的小分子结构与这个三维构象做重叠比较,找到了武田结构的
欠缺,然后对它们进行改造,使它们更接近血管紧张肽-Ⅱ的空间
构象。这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在看似理性的方法论中有相当比
例的经验工作、化学修饰和生物测试,工作量超过50人年。
最终,他们找到了第一个有口服活性的血管紧张肽-Ⅱ受体拮
抗剂——氯沙坦(Losartan)。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拮抗剂仅在
一种类型的检测中表现出活性,而在另一种类型中则没有。相
反,其他公司报道的拮抗剂却显示出了相反的活性,拮抗第二种
类型的检测,而不是第一种。相比之下,肌丙抗增压素在两种分
析中都有一定的活性。因此,几个不同的科研小组得出了相同的
结论:很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血管紧张肽-Ⅱ受体亚型,调节血压
的功能主要来自其中的一个亚型,而且正好就是氯沙坦选择拮抗
的那个亚型!
[30]
默沙东从杜邦制药接手了氯沙坦的开发,经过临床试验后,在1995年把新一代的降压药氯沙坦(商品名科素亚)推上了市
场,而海捷亚则是科素亚与利尿型降压药氢氯噻嗪
(Hydrochlorothiazide)的复方制剂,双管齐下,效果更佳。
研发出疗效更好、更安全的更优专利药,首先获益的应该是
患者,他们的病情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他们的生活质量会进一
步提高,然后才是制药公司。2011年10月初稿于新泽西
2017年11月修改稿于新泽西第六章 当“头号杀手”遇上“头号大药”
从胆固醇假说到他汀4S经典
仔细看一下这三个化学结构式。
图6-1 美伐他汀、洛伐他汀和辛伐他汀化学结构式
看出区别来了吗?
这三个化合物都跟胆固醇(Cholesterol)有关系。化合物1叫
美伐他汀(Mevastatin),是一个天然产物;化合物2叫洛伐他汀
(Lovastatin),也是一个天然产物;化合物3叫辛伐他汀
(Simvastatin),是洛伐他汀的人工衍生物。它们之间的区别就
是一个甲基,这是以碳原子为骨架的有机化合物的最小结构单
元。
[31]
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无足轻重、几乎可以被忽略的变
化,给这三个化合物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魏尔啸大胆立说
近年来,胆固醇的名声是越来越坏了。高胆固醇已经成了亚
健康的代名词。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印着“不含胆固醇”字样的各种食品,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高密度”与“低密度”的区别:前者
是“好”胆固醇,而后者是“坏”胆固醇,越少越好。其实,这对胆
固醇来说挺冤枉的。
相传,这个现在家喻户晓的油脂性化学物质最早是由法国化
学家塞尔(Salle)在1769年从胆石(Gallstones)中发现的,但是
到了1815年才有正式的文献记载,被法国化学家谢瑞尔
(Chevreul)命名为“胆固醇”。胆固醇是哺乳类动物细胞膜的基
本结构单元之一,对细胞膜的通透性和流动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胆固醇也是生物合成各种甾体类激素、胆汁酸(Bile acids)
以及维生素D的前体。人体内胆固醇相对含量最高的器官是大
脑,传递信息的神经细胞膜的结构与功能都与胆固醇密切相关。
毫不夸张地讲,胆固醇是人和动物体内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化
学物质。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成年人体内胆固醇的总量在35克左右,分外源性和内源性两种。外源性胆固醇来自食物,每天的摄入量
一般在200毫克~300毫克(素食者低于此量);内源性胆固醇则
是在肝脏中生物合成,每天大约有1000毫克。食物里的胆固醇一
般不容易被吸收,即便有少量被吸收了,它还是会对内源性胆固
醇的生物合成产生抑制作用,从而维持体内胆固醇总量的相对稳
定,所以从食物中摄取的胆固醇对人体内胆固醇的总量以及血液
里的游离胆固醇浓度的影响都不大,这就是调节饮食对降低胆固
醇的作用一般都不大的原因。
胆固醇与冠状动脉硬化和瘀塞之间的联系很早就引起了医学
界的注意,1856年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Virchow)就提出了冠
心病的“胆固醇假说”(Cholesterol hypothesis)
[32]。根据病理解
剖的发现,魏尔啸认为血液里的游离胆固醇在动脉血管壁上的沉
积是造成动脉血管硬化和冠心病的直接原因。这是一个超越时代
的大胆假设,一直到100年后的1956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研究人
员从酵母菌的提取物中分离出了羟甲戊酸(Mevalonic acid),随
后又证实了甲羟戊酸是胆固醇生物合成的中间产物,基础医学对于胆固醇代谢和调控的研究才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其后的几十年
间,人们对胆固醇的生物合成和转移的研究,对摄入胆固醇的吸
收和代谢的认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胆固醇与冠心病之间的联系
也从一个原始的假说逐步上升为医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
远藤章咬定青山
1959年,德国马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在胆固醇生物合
成中起重要作用的物质——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HMG-
CoA reductase)。内源性胆固醇是在肝脏中由乙酸经26步酶催化
的生物反应合成的,其决速步骤就是由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
酶催化的,从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HMG-CoA)到甲羟戊酸根
(Mevalonate)的转化。当外源性胆固醇降低时,羟甲基戊二酰
辅酶A还原酶的表达和活性就会增强,在肝脏内合成更多的内源
性胆固醇,以弥补不足。可见要降低血液里的胆固醇含量,单靠
改变饮食结构、降低摄入量是不够的。于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们开始积极地寻找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的抑制剂。
到哪里去找这种酶的抑制剂呢?日本生物化学家远藤章
(Akira Endo)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在自然界里,有很多微生物
的生长是依赖于胆固醇和类萜化合物的。对于这类微生物来说,胆固醇的生物合成是它们的生命线,而抑制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
还原酶的活性对它们则是致命的。远藤认为,自然界里一定存在
着另一些微生物,它们在生存竞争中以抑制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
还原酶的活性为目标,用“化学武器”去攻击那些依赖胆固醇的微
生物,成为它们的克星,而这种“化学武器”很有可能就是天然的
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
大自然无奇不有,我们应该从哪里下手呢?抱着这个坚定的
信念,凭借他和同行们对于不同微生物的充分了解,远藤领导日
本三共制药公司的团队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辛辛苦苦地筛选了
6000多种不同的微生物。1973年,他们终于从桔青霉菌
(Penicillium citrinum)中找到了第一个天然的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美伐他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是人类
征服其“第一杀手”冠心病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远藤章因此获得
了2006年日本国际奖
[33]
和2008年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
远藤章三共团队的新发现引起了制药界同行的极大兴趣,寻
找天然的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立刻成了新药研发的
大热门。1978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科研团队依样画葫芦,在筛选
了5000多个发酵提取物的样品后,从土曲霉菌(Aspergillus
terreus)中分离出了一个几乎与美伐他汀完全一样的天然产物
——洛伐他汀。两者唯一的区别是,洛伐他汀的3号位上多了一
个甲基。不难想象,与美伐他汀一样,洛伐他汀也是一个高效的
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
经过临床前的药效研究(Efficacy study)和安全评估之后,三共制药率先开始了美伐他汀的临床试验,默沙东的洛伐他汀紧
随其后。但好景不长,1980年,美伐他汀的厄运降临了,一直进
展顺利的临床试验戛然而止了。
默沙东拨云见日
尽管没有正式发表的研究报告,但来自三共制药的内部消息
显示,在为期15周的动物安评试验中,长期服用高剂量美伐他汀
的实验用狗患恶性肿瘤的比例升高。其实任何东西吃多了都可能
会有问题,头疼腰酸等各种轻微的副作用,几乎每个药都有,关
键是看它有多大的安全指数。
[34]
即使是血压升高、肝功能异常
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只要它们是可逆的,即停药后可在短期内
恢复正常,没有后遗症,还是可以在足够的安全指数下谨慎处理
的。但是癌症就不一样了,首先它不可逆,其次它威胁生命。假
设长期服用剂量为每千克体重100毫克时狗患癌症的比例增长了
10%,你愿意冒这个风险吗?三共制药不愿意,药检机构也不可
能批准通过,所以只能停止临床试验。消息传到默沙东,化学结构上只多了一个甲基的洛伐他汀的
开发也无法继续了,因为人们自然而然会推断:两者的化学结构
和生物活性都如此相近,估计毒性也差不到哪里去。为了这件
事,时任默沙东新药研究院主席、资深副总裁的瓦杰洛斯博士几
次亲自前往日本,试图与三共制药联手,共享资源,共同研究美
伐他汀的毒理,但是都被三共制药婉拒了。在默沙东内部,上上
下下对他汀类药物的前景也不乐观。是整个他汀类药物出了问
题,还是只有个别的他汀有问题?
科研需要直觉,但更需要数据。直觉告诉我们,洛伐他汀很
可能有类似于美伐他汀的毒性,但是我们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数
据。停止了临床试验后,默沙东又重新审定了洛伐他汀的安评结
果,在继续进行长期和严格的毒性试验的同时,开始寻找结构上
不同于这两个他汀的新型化合物。
值得庆幸的是,为期两年高剂量的动物毒性试验没有发现洛
伐他汀有任何致癌的迹象,经各方专家的咨询和评审通过,洛伐
他汀的临床试验于1983年底重新启动。数据结果显示,洛伐他汀
对人体也是安全的,它说明了抑制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本
身尽管在高剂量时也有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极少部分患者
会出现肝功能的变化、肌肉的疼痛和痉挛等,但是不会致癌,美
伐他汀的致癌性只是个例,就因为它缺了一个关键性的甲基。
1987年,洛伐他汀经FDA批准成为第一个上市的他汀类药物,获
得了巨大成功。
这个小小的甲基,不但挽救了洛伐他汀,也挽救了整个他汀
类药物,使之成为历史上的“头号大药”——销售金额最大的处方
药物,因为他汀类药物所面对的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冠
心病。
冠心病潜滋暗长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它的作用就好比是一个永不停息的泵,随着心肌的每次收缩将携带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液经主动脉
输送到全身,以供各器官和组织细胞代谢需要。那么,心脏自身
的氧气和营养又如何得到呢?当然也是从心脏得到的。原来,在
主动脉的根部分出了一条支脉,绕了一个小弯后回到心脏,那就
是负责心脏本身供血的动脉,它的弯形如冠,所以被称为冠状动
脉。
由于脂质代谢不正常,血液中的脂质沉积在原本光滑的动脉
内膜上,形成一些类似粥样物质的白色斑块,造成动脉的硬化和
淤塞,称为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这样的病变如果发生在冠状动脉
里,那就成了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
因为冠状动脉的硬化和淤塞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也没有特
征性的临床表现,所以早期诊断很困难,除非做高分辨率的心血
管造影,否则不会被发现。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由于肢体功
能的(正常)下降,大运动量的体力活动逐步减少,对心脏功能
的要求也逐年降低,即使在心脏本身供血不足的情况下仍能维持
正常的生活起居。有不少病例显示,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淤塞
高达90%以上,真可说已经是“命悬一线”,但仍然无明显特异性
症状,偶发的胸闷气短被认为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正因为如
此,冠心病潜在的危险在没有提防的情况下不断地滋长。
由于长期供血不足,冠心病患者的心肌已经变得很脆弱,承
受力大大降低,一些原本习以为常的活动,比如挪动家具、排
便、看紧张的球赛、喝酒、受惊吓等,都会在瞬间超出供血不足
的心脏的负荷。沉积在冠状动脉内壁上的粥样斑块大多数是稳定
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不稳定的“易损斑块”,在心肌活动异常时这
些易损斑块有可能会脱落下来,阻塞血管,引起心肌梗死,在很
多情况下是致命的。
心梗的直接原因是动脉血管的老化和阻塞,而动脉血管老化
和阻塞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就是高胆固醇。舒降之打造经典
在进行洛伐他汀临床试验的同时,默沙东实验室的科学家们
毫不放松,又找到了一个更加安全有效的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
原酶抑制剂,这便是后来的辛伐他汀(化合物3)。辛伐他汀与
洛伐他汀的差别在于:又多了一个甲基。
有了美伐他汀的先例,人们自然会问:在洛伐他汀上加了一
个甲基之后会不会引起一些新的副作用?所以辛伐他汀的药效和
安评必须全部从头来过,不得有一点马虎。实验数据显示,辛伐
他汀是一个功能强大的降胆固醇药物,最高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LDL)50%。其剂量为5~80毫克,对于高密度脂蛋白
(HDL)及甘油三酯的水平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除了他汀类药物
对极少数患者的一些常见的副作用外,辛伐他汀是一个安全且更
有效的降胆固醇新药,于1991年底获得FDA的上市批文,中文商
品名为“舒降之”(Zocor)。
他汀类药物能有效地降低人体血液里的游离胆固醇浓度,但
游离胆固醇只是一个生物标记物(Biomarker)。魏尔啸160年前
的“胆固醇假说”能不能成立?他汀类药物到底能不能减少冠心病
的发病率呢?1994年,默沙东公布了著名的“4S”临床研究结果,为他汀类药物的普遍应用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科学依据。
该临床研究项目的全称为“斯堪的纳维亚辛伐他汀存活率研
究”(Scandinavia simvastatin survival study,简称4S),为期5
年,跟踪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
的冠心病患者共4444人。结果显示,服用辛伐他汀的患者血液里
的游离胆固醇含量平均降低了35%,更重要的是,与对照组相
比,可能的心梗死亡率降低了42%,首次为“胆固醇假说”提供了
最直接的实验数据,成为冠心病临床研究领域里的经典。基
于“4S”临床研究结果,医学界普遍认为,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可以大大降低冠心病患者心梗或者脑梗的风险,延年益寿。中老
年人即使未患冠心病,如果血液里游离胆固醇的浓度偏高,也应该服用他汀类药物,减少或延缓心血管的硬化和阻塞,提高生活
质量。正因为如此,能有效抑制内源性胆固醇合成的他汀类降胆
固醇药物很快成为历史上的“头号大药”,这一类药物的全球年销
售总额高达数百亿美元。
一个小小的甲基,可以把美伐他汀打入冷宫;同样是一个小
小的甲基,也可以使辛伐他汀(舒降之)成为预防和治疗冠心病
的经典。遗憾的是,我们目前还无法预测,哪一个甲基(或是任
何其他基团)会带来毒性或者副作用,哪一个甲基能提高安全系
数或者药效。我们不能轻信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修饰和改动,安
全评估报告可能要泼你一头冷水;我们也不能放弃几乎相同的衍
生物,药效研究的结果也许会给你一个惊喜。
我们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益适纯一波四折
不难想象,由于他汀的巨大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降
胆固醇药物的研究成了各大制药公司的热门。
同在新泽西州,距离默沙东实验室不远的先灵葆雅制药公司
(2009年被默沙东兼并)当然也不例外,他们锁定了冠心病研究
领域的另一个热门靶点——乙酰辅酶A胆固醇酰基转移酶(Acyl-
CoA cholesterol acyltransferase,简称ACAT)。当时有文献报道
认为,对ACAT的抑制能阻止胃肠道对外源性胆固醇的吸收,从
而与抑制内源性胆固醇合成的他汀类药物起到互补的作用。
先灵葆雅的ACAT抑制剂项目在启动后马上就遇到了麻烦。
团队科研人员精心设计出来的在纸面上看起来很合理的新型化合
物在一轮又一轮的生物测试中都没有呈现出预期的生物活性,令
人失望。一个有心的实验员,把本来应该丢进废料桶的副产物分
离纯化之后送去做了测试,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这个产率不
到5%的副产物不仅在体外生物测试中显示出了相当的活性,而且在高剂量的动物模型中也有一定的药效。如果说测试一个非设计
的副产物已经是小概率事件,那么这个副产物不但有体外的生物
活性,而且还有动物模型中的药效,就是小之又小的概率了。
先导化合物被意外地发现了。以这个有活性的副产物作为模
板,研究人员接着一轮一轮地设计新的化合物,试图优化这个先
导化合物。虽然这些新化合物对ACAT的抑制活性越来越高,但
是在动物模型实验中的效果(胆固醇下降)不见有什么增强,停
留在30%左右,远远低于适合临床开发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
下,公司高层慎重地评审了这个项目,认为该靶点与胆固醇的吸
收没什么相关性,决定停止ACAT抑制剂项目,将有限的资源投
入其他更有希望的项目上。公司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的研究结
果也证实了ACAT与胆固醇的吸收确实没有必然的联系。
辛辛苦苦做了几年的项目要下马,项目研究人员当然不高
兴,他们所能做的便是将这个项目的实验数据整理成文,争取在
科学杂志上发表。在整理这些数据和撰写论文时,研究人员经常
需要补充少量化合物及其数据。于是,在部门领导点头之后,一
名药物化学人员在项目被宣布下马之后又补做了2对(4个)新的
化合物,打算在生物测试之后,将这些新的数据填写到论文的表
格里去发表。尽管体外测试的结果跟预计的差不多,但在动物模
型实验中意想不到的一幕又出现了:其中两个新化合物的药效比
所有已知的化合物高出了很多倍。新的突破口又一次被意外地发
现了。
在对这个意想不到的补充化合物进行代谢研究时,药理研究
人员发现,该化合物所产生的药效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远远超过
根据它的体内半衰期所预计的有效时间。也就是说,当血液里药
物浓度下降至有效浓度以下时,它的药效却仍然存在。怎么会这
样呢?经过研究人员追根溯源的仔细研究后,在用药后的仓鼠的
胆管里发现了几个比药物本身活性更高的代谢产物。在新药研发
里,这样的好事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了这个可遇而不可求
的发现,团队的科研人员通过化学修饰,合成出了体内活性比原先的临床候选药物高出400倍的新化合物——益适纯(Zetia)。
因为益适纯也只是在胃肠道和胆管里来回周转,只有很少量进入
血液循环和身体的其他脏器,所以它的安全性也非常之好。
随着临床研究的顺利进行,公司开始着手准备向FDA报批申
请材料,可是项目团队的研究人员又犯难了:益适纯所作用的体
内生物靶标肯定不是当初立项时的ACAT,那到底是什么呢?在
正常情况下,FDA一般是不会批准生物靶标未知的新药上市的,益适纯又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的临床前动物实验与临床试验的结
果很有说服力,疗效显著,安全指数好,适应面广,与他汀类药
物能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后来先灵葆雅与默沙东合作研发益适
纯与舒降之的复方制剂,在合作过程中,两个公司的联合研究团
队也最终搞清楚了益适纯的生物靶标是PNC1L1——胃肠道里一
个重要的胆固醇输送蛋白。
那是益适纯上市(2002年)以后好几年的事了。
葆至能更上层楼
如果说每一个成功的新药研发项目都包含着一点幸运的因
素,那么益适纯的研发过程中幸运的因素就远远不止这一点点
了。但仅仅靠撞大运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与
实践,正因为如此,益适纯的研发团队不但歪打正着地创造出了
一个又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还及时抓住了这些一闪即逝的机
会,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成功。
从机理上看,益适纯抑制胃肠道对外源性胆固醇的吸收,应
该能与抑制内源性胆固醇合成的他汀类药物起到互补的作用,所
以当益适纯还在临床试验阶段时,默沙东就拿着舒降之上门求合
作去了。
两种药物联合使用,最坏的可能性是出现药物相互作用
(Drug-drug interaction),不但药效会受到影响,还有可能出现毒副作用;最常见的结果是既不互补也不互损,1加1等于2;最
好的结果则是互补的协同效应(Synergistic effect),出现1加1大
于2的结果。益适纯与舒降之联合使用的复方制剂葆至能(商品
名Vytorin)就是这种最好的结果,非但没有相互干扰,而且还显
示了很好的协同效应。
科学是严格的。益适纯与舒降之联合使用可以有效地降低胆
固醇,并不等于也一定能降低冠心病患者心梗的风险。换句话
说,默沙东经典的4S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扩展到益适纯与舒降之
的联合使用,只有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才能说明问题,于是乎,又
一个长达9年的临床试验开始了。
2014年,美国心脏协会公布了默沙东制药名为“IMPROVE-
IT”的临床试验结果,数据显示,舒降之与益适纯的复合制剂葆
至能可显著减少高危冠心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益适纯与舒降之
的互补性使得葆至能非常适用于对他汀类药物敏感度较低的患
者,只要用相对较低的剂量就能将他们血液里的胆固醇控制在健
康的水平。葆至能可以同时抑制胆固醇的内源性合成与外源性吸
收,在高胆固醇和冠心病的治疗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比
例已经逐步上升到接近50%,在同一时期内,这个年龄组的心脏
病死亡率持续显著下降。
[35]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吸烟人口
的下降,饮食更为健康(至少在某些方面),心脏病治疗的改
善,心梗紧急治疗更为及时,等等。尽管我们很难把这些变化所
带来的效果一一区分开来,但是毫无疑问,服用他汀类药物所带
来的整体人群的胆固醇水平降低一定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2011年6月初稿于新泽西
2017年7月修改稿于上海第七章 “是药三分毒”的背后
从原创的顺尔宁到它的仿制药
是药三分毒,安全与有效是新药研发贯穿始终、相互依存的
两个对立面。
现在每一个药物的说明书上除了适应证与用药剂量之外,一
定会有好几条有关副作用的警告,严重的还会有“黑框警告”。就
拿最最常见的阿司匹林来说吧,在市场上这么多年了,大概没有
人还会认为服用阿司匹林有什么不安全的,但它的说明书上清清
楚楚地写着:服用此药有可能导致胃肠道出血。最近的一项来自
意大利的跟踪研究
[36]
数据显示,在18.6万长期服用低剂量阿司
匹林的人群里,胃肠道出血的有2300个病例(占1.2%),脑出血
的有1300个病例(占0.7%)。
安全指数:在药效与毒副作用之间
从辩证法的角度讲,能把人治好的东西也一定能把人治坏,就看你怎么治,治到什么程度。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
基辛格博士在巴基斯坦访问期间对外称病住院三天,其实却在秘
密访问中国。消息公布之后,有传闻说基辛格当时真的病了,在
北京期间听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到协和医院接受了针灸治疗,结
果针到病除,由此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针灸热”。当时针灸被说得
神乎其神,很重要的一条理由是,它号称绝对没有副作用。其
实,这种说法既不符合辩证法,也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当年金
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还没有流入内地,要不然以针刺穴而置人于死地的武林高手和民间故事应该是信手拈来的。针灸治病的机
理目前还不清楚,但相信它有(不只是心理)作用的人必须承
认,针灸一定要通过改变人体内的某个生物过程才会有疗效。这
个生物过程既然能改变人体的状态,从病态变回到正常态,那么
它一定也有可能反过来,把一个人从正常态变为病态。
药物治疗是用化学物质(包括各种无机盐、有机小分子和生
物大分子等)来改变人体内某个特定的生物过程。在任何一个时
刻,人体内都有成千上万个化学反应在同时进行着,这是维系生
命所必需的。所谓“正常态”就是由这些化学反应而决定的生物过
程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从表征上讲,心跳不能太快也不能太
慢,血压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等等;表现在分子水平上,就是
功能性蛋白质(包括受体、酶、离子通道、转运蛋白等)的表达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各种代谢和循环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
旦超出了这个正常范围,就会出现“病变”,人体也就进入了“病
态”。
造成人体病变的原因有很多,比如2型糖尿病,是因为人体
内的葡萄糖代谢发生了紊乱,使得血糖持续升高,从而引起一系
列严重的并发症。通过服用西格列汀等新型糖尿病药物,可以改
变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代谢,把血糖降下来,将其控制在正常范
围内。
[37]
但是,如果哪一个药物把血糖降得太多了,就有可能
给病人带来生命危险。所以制药界还有一句行话,“剂量造成毒
药”(Dose makes poison),什么东西吃多了,都有可能给身体带
来不良后果,药吃过量了,当然就更是如此了。
怎么吃药才算安全呢?制药界定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安全指数(Safety index),有时也称“治疗指
数”(Therapeutic index),或者“安全窗口”(Safety window),它是最高安全剂量(又称最高无副作用剂量)与最低有效剂量之
间的比值。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临床试验药物的最低有效剂量是
每千克体重2毫克,而在临床试验中没有观察到副作用的最高剂
量是每千克体重40毫克,那么这个试验药物的安全指数就是402=20(一般用“20X”表示20倍的意思)。安全指数是根据临床
试验的数据计算出来的,是参与临床试验人群的统计数值。对于
不同的副作用,安全指数一般来说是不一样的,比如引起轻微头
疼的指数是10X,而引起血压升高的指数则可能是50X。对于不
同的人种、不同的性别以及不同的年龄组,同一种药物的安全指
数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落实到个体病人,每种药物的安全指数
还会有上下波动,但是绝大多数都应该在统计误差的范围之内。
在原创新药的研发过程中,安全指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杆。安
全指数越高的药,用药的允许误差就越大,适用的人群就越广。
一种新药若能被国家监管部门批准用于婴幼儿,它的安全指数一
定是很高的,默沙东的原创新药顺尔宁(Singulair
TM ,药名孟鲁
司特[Montelukast sodium])就是少数几类被批准用于治疗婴幼
儿哮喘病和过敏症的药物。
哮喘病:在成年人与婴幼儿之间
哮喘病(简称哮喘)是一种很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少年儿童
中最多发的慢性病。
哮喘(Asthma)的英文词源于古希腊文,意指“急促的呼
吸”,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50年希波克拉底的描述中。几百年后,古希腊医学家盖伦撰文,第一次提到了哮喘是因部分或整个支气
管阻碍所造成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8月在其官方网站上
更新的数据,目前全球哮喘病患者大约有2.35亿,与哮喘相关的
死亡有80%发生在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
中心官方网站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成年哮喘病患者人数
接近2000万,平均每12人中有1人患病;儿童哮喘病患者人数约
700万,平均每11名儿童中有1人患病。年龄组18岁以下的发病率
(9.6%)明显高于年龄组18岁以上的发病率(7.7%),而发病率
最高的年龄组是5~17岁,接近11%。中国哮喘联盟发布的一份报
告显示,我国哮喘病患者多达3000万,发病率高达1.24%,而在
众多的哮喘病患者中,儿童就占600万,发病率为1.97%,这意味着每100名儿童中就有2名哮喘患者。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加上一
些偏远地区的医疗条件较差,应当还有相当多的哮喘病患者尚未
被确诊,所以实际患病人数估计远远超出4000万,其中约有700
万儿童饱受哮喘困扰。在环境污染严重的今天,哮喘的发病率还
会不断上升。
哮喘病是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重要疾病,如果治疗不及时,不规范,哮喘的急性发作甚至可能致命。我们这一代人都非常熟
悉和喜爱的一代歌后邓丽君女士就是因为哮喘突发,抢救不及时
而离世的。2002-2007年,美国每年用于治疗哮喘病的费用平均高
达560亿美元,经济损失巨大。哮喘病多发于学龄儿童中,全美
国的中小学生因为发哮喘而不能上学的天数每年累计大约有1500
万天。
哮喘病是一种支气管慢性炎症性疾病,这种慢性炎症导致孩
子的气管过分敏感,当受到各种因素的刺激时,过分敏感的气管
发生反应,就会出现哮喘症状。发病内因包括儿童本身特应性体
质、遗传特性等;外因则包括空气污染、食物过敏、营养不均、宠物过敏等。其中环境污染的关联最为突出。PM2.5被认为会导
致咳嗽、呼吸困难、肺部功能降低、加重哮喘等疾病。这些细小
颗粒通过呼吸道,部分没有被过滤掉的就沉积在人体里,从而危
害健康。另外,季节变换时,尤其是春季,也是儿童哮喘的高发
期,会出现反复发作性喘息、胸闷、咳嗽乃至呼吸困难。患儿不
能参加正常的学习和课外活动,给家庭带来了较大的身心负担。
从20世纪开始,支气管扩张剂一直是治疗哮喘病的重要手
段,主要有抗胆碱类药物(Anticholinergic agent),如溴化异丙
阿托品(Ipratropium bromide)和β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β2
adrenergic receptor agonist),沙丁胺醇(Albuterol)和特布他林
(Terbutaline)等药物。直到20世纪60年代,医药学家们才发现
哮喘不只是单纯的支气管挛缩,而是一系列的炎症反应,因此才
将消炎药加入哮喘病的治疗中。目前,以顺尔宁(孟鲁司特)为
代表的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可以抑制气道炎症,降低气管敏感性,减少病毒诱导的间歇性喘息,尤其适用于治疗同时患有过敏性鼻
炎的哮喘。
顺尔宁:在大胆创新与谨慎验证之间
20世纪30年代,两位澳大利亚生理学家从豚鼠的肺部发现了
一类“慢反应物质”(Slow reacting substance,简称SRS),到了70
年代,类似的“慢反应物质”在人的肺部也被发现了,而且有迹象
表明,这些“慢反应物质”很可能在哮喘的发病过程中起着很重要
的作用。尽管来源很有限,稳定性也不好,但很多制药公司还是
开始了对“慢反应物质”的研究,默沙东也不例外。
直到70年代末期,这些“慢反应物质”的结构才被逐一确定下
来,并被统一命名为“白三烯”
[38]
(Leukotriene,简称LT)类化
合物,随后完成的人工全合成又解决了来源短缺的问题,使得白
三烯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而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有可能用于哮喘病
治疗这一大胆的假设也为更多的医药研究人员所接受。要知道,当时白三烯的受体还没有被发现,直到90年代末期,默沙东的第
一个白三烯受体拮抗剂药物顺尔宁上市后,白三烯的受体才首次
被提取出来。
在没有纯化的白三烯受体的情况下,所有实验都只能在细胞
或组织里进行,通量低,稳定性也差。面对这样的挑战,位于加
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郊的默沙东实验室福斯特研究所
(Merck Frosst)的科研团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将第一代的
两个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候选药物先后推上了临床试验,一个做口
服药,另一个做喷雾吸入制剂,但结果差不多,都不尽如人意。
这两个化合物虽然都有一点点统计意义上的药效,但远远没有达
到临床应用的标准。面对挫折,默沙东蒙特利尔的研究团队决定
寻找活性更高的白三烯受体拮抗剂,以期达到显著的临床效果。
1989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第二代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候选药物
进入了临床试验。因为活性和口服生物利用度的大大提高,在为期6周的药效试验中,哮喘病患者的肺活量有所提高,肾上腺素
受体激动剂的使用减少,喘息、胸闷乃至呼吸困难等典型哮喘病
症状都有了明显改善,实现了临床的概念证明(Clinical proof of
concept,简称Clinical POC)。预期的药效达到了,但副作用也
随之而来。在高剂量的大鼠安评试验中,这个候选药物引起了意
想不到的肝肿大,没有了足够的安全指数,临床试验也只好立刻
下马了。
进一步的毒理研究发现,大鼠的肝肿大是由于肝脏过氧物酶
体(Peroxisome)的增殖引起的。有没有可能找到既有明显药
效,又不会引起肝肿大的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呢?带着这个疑问,默沙东实验室的科研人员重新回到实验室,继续埋头苦干,在安
全与有效的夹缝里,寻找新一代的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功夫不负
有心人,1991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第三代第四个白三烯受体拮抗剂
候选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口服剂量从2毫克一直到
800毫克都没有发现副作用,而有效的口服剂量只要5~10毫克左
右,安全指数之高可见一斑。在随即展开的儿科临床研究中,这
个候选药物的咀嚼剂型在婴幼儿患者中也同样显示了良好的疗效
和安全性,而且不影响婴幼儿的生长速率。
临床研究的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了默沙东福斯特研究所,为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的研发一起辛勤工作了18年的科研团队又一
次聚到了小会议室里。他们再一次绞尽脑汁,为这个即将诞生的
抗哮喘新药命名。热议之后,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个未来的新药
叫作“孟鲁司特”(Montelukast)
[39]
,以纪念它的诞生地——蒙
特利尔(Montreal)。1998年2月,顺尔宁(孟鲁司特)上市,被
批准用于成年人以及6~14岁儿童。2000年6月,顺尔宁又被FDA
进一步批准用于1岁以上的婴儿患者。
等效性:在原创药与仿制药之间
2012年8月3日,默沙东原创的用于治疗哮喘与过敏的品牌药孟鲁司特的化合物发明专利在美国到期了。
[40]
就在同一天,FDA批准了第一个孟鲁司特的非专利仿制药(Generic drug)。 [41]
从原来的独家生产,进入了多家竞争的新阶段。竞争无疑会
给消费者带来益处,但是大家自然而然地会问:仿制药与原创药
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仿制药与原创药里的有效成分在分子的水平上是完全一样
的,也就是说,有效成分是同样的化学分子。但是,尽管仿制药
里含有相同等量的有效成分,而且纯度检验也达到要求,但还是
有可能在疗效和副作用上与原创药有所不同。如何把一个化学分
子做成药剂还是颇有讲究的。
一般来说,原创药物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专利是化合物发
明专利,做仿制药这个专利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必须等到这个专
利有效期届满。但是所有的原创药物除了化合物发明专利之外,一定还会有工艺流程的专利、晶型的专利、制剂的专利等,而且
它们的有效期都会在化合物发明专利之后,比如孟鲁司特的口服
液制剂(Oral granuales sprinkle formulation)的发明专利要到2022
年才到期。
这些“二线专利”虽然给仿制药的生产设置了壁垒,但它们的
保护是有限的,通俗地讲,就是可以“绕过去”的。首先,仿制药
的生产厂家会建立自己的工艺流程。由于工艺流程的不同,生产
出来的有效成分尽管在纯度上达到了要求,但是在杂质分布等其
他指标上很难做到与原创药完全一样,如果引进了新的主要杂
质,就必须做鉴定和安评。工艺通过了,还要挑选专利保护之外
的晶型。不同的晶型在体内溶解和吸收的速率是很不一样的,如
果你不信,就拿点绵白糖和冰糖放在水里试试,虽然都是糖,但
溶解的速率相差很大。原创药的专利晶型在溶解性、稳定性和生
产成本等各个方面肯定都有优势。仿制药的生产厂家没有别的办
法,只能在其他的晶型里挑选,然后通过制剂的研究,争取达
到“生物等效”。所谓生物等效性,就是仿制药与原创药的临床药代动力学比
较数据。为了保证仿制药与原创药有同等的药效和安全性,仿制
药的生产厂商必须在报批时向药监局提供“生物等效性”(Bio-
equivalency,简称BE)的临床数据。BE这个术语近两年在国内
医药界变得非常流行。只有在仿制药的药代动力学指标进入了原
创药的误差范围之内,才能宣称该仿制药与原创药具有“生物等
效性”,药监局才会批准上市。这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临床试
验,所以研发仿制药的成本远远低于原创药,药品的价格也就会
远远低于原创药。大量低价仿制药的上市可以让更多的患者获得
及时的治疗,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医保环节的经济负担。
因为生物等效性的临床试验是短期的,而原创药在化合物发
明专利到期之时,已经积累了大量长期临床使用的数据,医药人
员对其药性、剂量、适用人群、可能发生的副作用等重要参数都
有很好的了解,所以用起来更放心一些,尽管在价格上要贵一
些。不光医药人员如此,广大患者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有
这个倾向,所以,拜尔生产的阿司匹林到现在仍旧是药房里最受
欢迎的。
固定剂型:在体重与剂量之间
目前,顺尔宁的剂量有10毫克和5毫克的片剂,适用于成年
人;有4毫克的片剂,适用于儿童;还有婴儿用悬浮液,出生6周
以上的婴儿就可以用了。
所有新药在临床前的动物研究期间,其用量都是按照实验动
物体重严格计算的,无一例外。药代动力学研究(药物进入体内
后都去哪了?)必须按体重计算用量,药效学(药物进入体内后
都干了啥?)也必须按体重计算用量。这样做有利于建立剂量的
相关性,消除因为体重不同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有利于不同种
类的实验动物之间的外推和换算。但是,一旦进入临床研究,按
照体重计算剂量的可操作性就没有了,药房是不可能给前来配药
的患者先称一下体重,然后计算出相应的剂量,当场配制药物的,所以只能是一个或几个预先设计好的固定剂量。
在临床研究的前期,因为健康的志愿者或患者人数相对较
少,挑选可以比较严格,特别瘦小,或是特别肥胖的人可以不入
选,所以用平均值(一般男性按60千克,女性按50千克)计算也
不会有大的出入。在做人体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时,还会有意识地
包括不同体重的受试者,获得药物与体重的相关性,以便在临床
研究的后期确定不同年龄组的不同剂量。
就拿顺尔宁来说,成人的用药剂量确定在5毫克和10毫克两
个固定剂量,但是根据药代动力学的数据,5毫克用于儿童保险
系数不够大,因为儿童的体重差别是很大的,为此,默沙东专门
开发了4毫克的片剂。你也许会问:5毫克与4毫克只差1毫克,真
的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如果说是100毫克与99毫克,那倒真是没多大差别,因为相
对误差才1%。但是5毫克与4毫克就不一样了,相对误差已经达到
了25%。一个1岁的哮喘患儿,本来身体发育就受到了影响,体重
偏低,再多吃25%的药物,结果就不好说了。
开发5毫克与4毫克两种片剂也把默沙东的化学工艺和制剂研
究水平推到了极致。试想一下,生产100万片4毫克的顺尔宁药
片,必须把每一片有效成分的误差范围控制在3.6~4.4毫克之内
(±10%),需要多高的工艺精度?中国目前的化学工艺研究进
步很快,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够以可持续的“绿色化学工艺”生
产出剂量精准、生物等效的优质仿制药。
由于像顺尔宁这样全年龄组的抗哮喘新药的使用,当今的治
疗手段可使接近80%的哮喘患者的病症得到非常有效的控制,使
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不受影响。国际卫生组织把每年5月份的
第一个周二定为世界哮喘日,旨在提醒公众对疾病的认识,提高
对哮喘的防治水平。
2012年12月初稿于上海2017年12月修改稿于新泽西OEBPSTextpart0011.xhtml
第八章 凝结中国科学家毕生心血的HPV疫
苗
从诺贝尔医学奖的基础研究到制药公司的创新产品
癌症在很多人心目中可能还是“不治之症”的代名词,尽管近
年来,随着基础医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医药界对于癌症的认识已
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对于癌症的治疗和预防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展。2006年,默沙东投放市场的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简称HPV)疫苗佳达修? (Gardasil
)就是其中一个通过
抗HPV感染而预防包括子宫颈癌(Cervical cancer)在内的多种疾
病的有效疫苗,这也是一个凝结着中国科学家周健博士毕生心血
的疫苗。
十年“钓鱼”,豪森教授找出子宫颈癌起因
大多数癌症的起因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女性子宫颈癌是一
个例外。早在1974年,德国海德堡癌症研究中心的海拉德·豪森
(Harald Hausen)教授就提出了HPV长期慢性感染会导致子宫颈
癌的假设。这个大胆的假设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因为
当时子宫颈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上。
豪森教授独辟蹊径,率领他的研究小组,潜心寻找子宫颈癌
细胞中人乳头瘤病毒的遗传物质DNA。他认为这些在癌细胞中的
病毒DNA很有可能处于长期的休眠状态,并不一定会复制新的病
毒体,这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豪森研究小组采用了一种俗称“钓鱼”的研究方法,把人工合成的已知DNA片断做上标
记,通过细胞内杂交,设法提取病毒的DNA。他们成功地从脚底
疣的细胞中找到了HPV的DNA片断,后来在皮肤疣的细胞中也找
到了。但是,当他们将同样的方法用于子宫颈癌细胞时却失败
了,没有找到HPV的DNA片断。豪森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气
馁,也没有怀疑他们当初的设想。考虑到病毒DNA不断变异的特
性,他们改进了传统的“钓鱼”方法,扩大搜索范围,经过十多年
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钓到了“大鱼”,在子宫颈癌的活
体切片里找到了HPV的DNA片断。
1983年,豪森教授首次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立刻引起学
术界的高度重视。随后的研究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
是由于HPV的持续性感染引起的,并且其中大约有70%的病例是
由HPV家族中的HPV-16和HPV-18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引起
的,而这两种型别正好就是豪森研究小组最初发现并克隆的型
别。豪森教授的这项研究证实了HPV的构成,阐明了HPV的致癌
机理,以及影响病毒存活和细胞转化的因素,为预防和治疗妇女
子宫颈癌奠定了理论基础。200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
员会决定授予豪森教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表彰他的研究成
果对于人类健康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持续感染,人乳头瘤病毒危害深远
HPV是一种属于乳突病毒科的乳突淋瘤空泡病毒A属,是球
形的DNA病毒,目前已经发现了200多个型别,其中至少有40个
型别是通过性接触在人群中传播的。HPV病毒的其他传播途径包
括密切接触、医源性感染(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防护不
当,造成自身感染或通过医务人员传给患者)和母婴传播(婴儿
通过孕妇产道时的密切接触)等。在已知的HPV型别中,大多数
不会引起被感染者的任何症状,而且感染期也相对短暂,被感染
者能在1~2年之内自愈,目前尚未发现长期遗留的不良影响。但
是,有少数被感染者会发展成持续性的感染,造成人体皮肤黏膜的鳞状上皮增殖,表现为寻常疣、生殖器疣(尖锐湿疣)等症
状,属于低危型HPV感染。低危型的HPV感染率非常普遍,关于
女性生殖道HPV感染的流行病情,据2003-2004年来自美国的国家
健康和营养研究课题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14~59岁的HPV总感
染率接近27%,也就是说,在这个年龄段里,每四个女性中就有
一人被感染!而在卫生条件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里,HPV的感
染率还会明显高于这个数字,所以HPV感染对女性造成的危害大
大超出了先前的估计。根据2007年发表的中国HPV感染的筛查报
告,[42]
在子宫颈癌高发的农村地区和大城市的5218名妇女中,20~54岁妇女的生殖道高危型HPV平均现患率相近,分别为
14.6%和13.8%,显著高于世界发达国家同年龄的现患率(5%~
10%)。尽管没有子宫颈癌的威胁,男性也同样被HPV感染所困
扰,生殖器疣会带来生活上的诸多不便,而且HPV也是肛门癌和
阴茎癌的主要感染源。
在被HPV持续性感染的女性中,有5%~10%会逐步恶化,引
起宫颈鳞形上皮不同程度的病变,发展成高危型的HPV感染,整
个过程通常要10~15年时间。这些进一步的病变有可能最终导致
恶性的子宫颈癌,成为危及妇女生命的恶性疾病,发病率仅次于
乳腺癌,居妇科恶性肿瘤的第二位。著名香港艺人梅艳芳就是因
患子宫颈癌英年早逝,年仅40岁,是演艺圈和众多粉丝的巨大损
失。2002年,由HPV感染而引发的癌症新病例估计超过56万,居
所有癌症感染源的首位。宫颈癌是女性中第四大常见癌症。根据
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官方网站的预计,2019
年美国将会有1.3万多例宫颈癌的新病例,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将超
过4000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数据,在全球范围内,2018年宫颈癌新发病例估计为57万例,占所有女性癌症的6.5%,其中大约90%的宫颈癌死亡发生在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约
9.89万例,死亡人数约3.05万,发病率和死亡率呈明显的上升趋
势,且子宫颈癌发病年轻化,由此可以推测高危型的HPV感染在
中国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精诚合作,中澳联手构筑病毒“空心汤团”
既然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是由高危型HPV持续感染引起
的,而防止病毒感染最有效的方法是接种疫苗,那么如果能研发
出预防HPV感染的疫苗,不但可以有效地降低子宫颈癌的发病
率,而且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与HPV感染相关疾病的传播。
本着这样一个基本的科学理念,澳大利亚墨尔本沃尔特伊莱扎医
学研究所的免疫学家伊恩·弗雷泽(Ian Frazer)教授与中国病毒
学家周健博士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HPV疫苗的研究。
1989年,已经小有名气的伊恩·弗雷泽教授到英国剑桥大学学
术休假。在那里,他幸运地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这就是来自
中国的青年访问学者周健博士。日后,功成名就的弗雷泽谈起这
段往事时非常感慨地说:“我在剑桥大学的学术休假,并没有学
到多少计划中想学的干细胞知识,却幸运地遇见了周健。我们开
始合作研究HPV并探讨研制疫苗的可能性,周健的贡献在病毒
学,我的贡献在免疫学。”
[43]
两人在剑桥的相遇是短暂的,弗雷
泽在返回墨尔本之前,热情邀请周健夫妇去澳大利亚工作。
周健博士1957年出生在杭州,中学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工厂里
做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周健考入温州医学院,成为一名本科
生,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并于1987年获得河南医科大学病理学
博士学位。在北京医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一年之后,他前往
英国剑桥大学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免疫学与癌症研究中心肿瘤病
毒实验室做访问学者,并与弗雷泽相识。
1990年,应弗雷泽教授的邀请,周健博士带着妻儿来到澳大
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免疫实验室,和弗雷泽共同研究HPV。起初的
大半年里,他们的合作研 ......
作?者 梁贵柏
责任编辑 刘免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76905
关注我们的微博: @译林出版社
意见反馈:@你好小巴鱼目录
CONTENTS
序言(一)
序言(二)
第一章 一桩“赔本买卖”
第二章 人类与细菌的“军备竞赛”
第三章 为了一个没有河盲症的世界
第四章 遭遇“黑天鹅”的有准备之人
第五章 从后继专利药到更优专利药
第六章 当“头号杀手”遇上“头号大药”
第七章 “是药三分毒”的背后
第八章 凝结中国科学家毕生心血的HPV疫苗
第九章 挑战新世纪的健康威胁
第十章 默沙东的中国缘
第十一章 “不抗癌”的抗癌新药
后记
注释序言(一)
我怀着强烈的兴趣阅读了梁贵柏博士撰写的《新药的故事》
大部分内容,对于目前非常活跃的生物医药领域,这是一本不可
多得的科普好书。
作者梁贵柏博士曾经在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工作多年,是新药
研发第一线的优秀科学家。梁博士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和长
期向业界前辈们学习的体会,以生动的笔触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从
抗生素到抗癌生物药等对人类健康有着重大影响的药物,以及它
们跌宕起伏的研发过程。
新药的创新,我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也落后于印度和古
巴等国家。我们可以从这本新药研发历史的科普书中体会到创新
的真谛。
首先,药物创新是一个艰苦的历程。什么是创新的动力?我
相信每一个原药创新的科学家,在研究开始时绝不是先想到这个
药研发出来后会给他带来多少利益,而是出于对“未知的未
知”或“已知的未知”的强烈好奇心,以及对广大患者,特别是完全
无助、在当时无药可治患者的强烈责任感,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
初期青霉素的产业化,艾滋病、河盲症药物的研发一样。科学家
对未知的好奇心,永远是他们执着追求的动力。其次,创新总是
青睐善于抓住“机遇”的人,偶然发现一只黑天鹅不放过,更深入
观察,就得出天鹅不等于白天鹅的结论。科学家常常不轻易放过
意想不到的现象与实验结果,再深入探讨,就会有新发现。再
次,坚持与执着是创新者最重要的素质。君不见,在本书提到的
创新药物中,有哪个不是通过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努力
创制成功的?我和台湾地区的一位学者合作研发一种抗实体瘤新
药,在他研究15年的基础上,又进行了25年研究,经过无数次失败及评审否决,我们均已年迈。三年前他因突发性脑卒中半身不
遂,曾想打退堂鼓,但看了这本书,我们要向书中的主人公学
习,看到曙光,坚持下去就可能胜利!最后,精益求精。20世纪
80年代,卡托普利已经是非常好的降血压药物了,但美中不足的
是,常有白细胞降低及皮疹的副作用,科学家继续努力,更有效
而且副作用小的依那普利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就问世了。
对于从事药物研究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来说,这是一本温故知
新的书。现代医药研发从磺胺、青霉素到帕博利珠单克隆抗体,经历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分子科学的飞速发展,集中体现了生物工
程技术最前沿的突破性成果,以及这些看似理论性和技术性的突
破如何被创造性地应用到健康领域,为人类造福。
对于政府官员、单位领导和企业家来说,这是一本具有现实
意义的、有大局观念的书。从抗艾滋病药物的研发开始,一直贯
穿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只要是老百姓急需的药物,哪怕价格
低,甚至没有利润,都要研发!
对于普通的社会公众来说,这是一本通俗易懂的书。作者用
非常通顺的语言,清晰地讲述了新药研发的史实和知识,同时也
融入了自己多年来的体会和思考。作为一名理科出身的资深科学
家,作者的文字素养可圈可点,尤其是在解释新药研发的科技背
景时,并不令人感到艰深和乏味,而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体验。
21世纪的新药研发仍将依赖于生命科学的突破性进展,需要
更多的投入,还需要有更多像《新药的故事》这样优秀的科普书
籍问世,从而提高公众的医药知识水平,使医药创新得到全社会
更广泛的关心和支持。2018年7月11日序言(二)
《新药的故事》经过作者辛勤的努力,即将付梓。我有机会
在出版前看到书稿,阅读之后有一种先睹为快的感觉,深感这是
一本难得的好书。
本书作者梁贵柏博士曾在美国默沙东公司从事新药研究十多
年,是一位新药研究领域的资深科技专家。他起初并没有想到要
写一本书,只是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认识,写了一些散篇的新药研
究的“故事”。后来越写越多,越写越深,结集成册,就形成了这
样一本多侧面立体展现近代人类社会与疾病抗争历史画卷的书
籍。
这本书叙述了人类面对各种疾病挑战开展新药研究的探索过
程,这是一个各国政府、人民、科技界和全社会都关心的主题。
在当代,创新药物的研究与开发集中体现了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
领域前沿的新成就与新突破,体现了多学科交叉的高新技术创新
与集成,是新世纪科技和经济国际竞争的焦点之一。20世纪下半
叶以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成果成为最激动人心的科学
成就之一。这些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使新药研究的面貌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推动药物研究与医药产业进入了一个革命性变化的
新时代,也使新药研究领域成为当代最受关注的科技创新领域之
一。本书讲述的新药研发故事,清晰地勾画了一些对人类健康产
生深刻影响的新药诞生的脉络,不仅涉及新药研究的科技问题,也涉及新药研究的方向遴选与决策、组织与管理问题,内涵深
厚,深入浅出。书中始终贯穿着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思路、科学
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体现了丰富的学术内容、严谨的科学逻
辑。这些对于新药研究领域的科技创新必将带来诸多深刻的启发
和教益。这是一本讲述科学研究的书,但是它又不限于科技本身,而
是真诚、富有感染力地表述了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这既包括科
技工作者探索未知的好奇心,“攻克顽疾,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也包括讲道义、讲责任的真正企业精神,书中讲述的伊维菌素捐
赠和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的故事可以讲是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在这
里看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两者的结合
既是一个科技工作者个人走向成功的必备要素,也是一个企业成
为“伟大的企业”的必由之路。
本书讲述了许多科学的史实和知识,但是并不艰深难读,也
不令人感到枯燥乏味。我打开这本书,浏览了开头的几行文字,就禁不住被深深吸引,很想一口气读下去。我想,这一方面是因
为作者在药物研究领域具有自身的创新实践和体验,而不是仅仅
停留在书本知识上;另一方面也是得益于他的文字素养。他能够
用生动、洗练的笔触,在清晰交代科技内容的同时,融入自己的
所思、所想,甚至包括人生的感悟,使内容有血有肉,也使文字
具备了一种隽永的风格。这就使读者的阅读过程成了一种愉快的
体验。
我在药物研究领域学习和工作了多年,看过不少有关药物研
究的书籍。我要说,这本书是非常独特的一本。我们读这本书,不仅可以学习知识,而且还能感受到人类的科学精神和不懈追
求。我相信这本书不仅适合药物研究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青年学
生阅读,事实上我觉得它适合更多人阅读,无论是政府官员、单
位领导、企业家,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都能从这本书中有所获
益。
2018年12月10日第一章 一桩“赔本买卖”
从抗艾滋病药物研发谈以人为本
60多年前,默沙东制药公司
[1]
时任总裁乔治·W.默克
(George W. Merck,1894—1957)说了一句名言,成为公司的座
右铭,一直被引用至今:“我们应该记住,医药是用于病人的。
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制药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利润,利润是随
之而来的。如果我们记住了这一点,它(利润)从来不会失约;
我们记得越清楚,它就来得越多。”
[2]
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它讲的是新药研发机构和研发人
员以人为本的责任与义务。默克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
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默克先生同意将独家开发链霉素
的专利无偿退还给罗格斯大学基金会,与其他药厂共同开发和生
产链霉素,有效阻止了全球性肺结核病的蔓延。
[3]
默克先生认
为,制药公司对社会的责任以及与学术界的良好关系和密切合作
比任何一种新药的利润都更重要。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全球化进
程中,追求利润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同时也意味着不断地开拓
新的市场,不断地满足社会的需求。但是,如何把握眼前的利润
和长远发展、人类健康之间的平衡是一个始终困扰制药界的难
题。
艾滋病阴云笼罩
1981年,美国纽约和旧金山的医生几乎同时发现了一种新的
奇怪病症,该病的患者会被诱发出一些常见于有免疫缺陷人群的
感染和癌症,所以被称为后天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简称艾滋病(AIDS)。这是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而且当时缺乏治疗手段,病人经确诊后得不到
有效的治疗,死亡率很高,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相当大的恐慌。
医学界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展开了全面深入的研究。1984年,美
国和法国科学家最先找到了致病的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简称HIV,又称艾滋病毒[AIDS
Virus])
[4]
,而如何有效阻止该病毒对人体免疫细胞的入侵,控制它的复制,并最终将其清除的重任也就义不容辞地落到了制
药界同仁的肩上。
1986年,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又称默沙东实验室[Merck
Research Laboratories])首席科学家爱德华·斯考尼克(Edward
Scolnick)博士宣布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默沙东西点研究所成
立专门的艾滋病研究室,研发抗艾滋病毒的新药,其他各大制药
公司也先后确立了抗艾滋病研究项目。然而,人们对艾滋病进一
步的认识给制药公司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艾滋病的传染途径主
要是血液传播、性接触(精液)传播和母婴传播,因此常见于吸
毒人群(交换针头)、同性恋者、性工作者以及靠卖血为生的发
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这样一来,不但抗艾滋病新药的市场将有
很大的局限,而且新药的价格也会受到相当大的挤压。默沙东制
药的内部资料显示,当时市场和财务部门对抗艾滋病新药的赢利
预测为负值。也就是说,即使默沙东的抗艾滋病新药研发成功,由于受市场和价格的限制,在其专利有效期内也不足以收回成
本。如果失败,当然是颗粒无收,全部投入都打水漂。因此,从
商业的角度看,无论怎么算,这好像都是一桩赔本的买卖。
“赔本买卖”
但“这不是一桩普通的买卖”,在2004年出版的回忆录《医
药、科学与默沙东公司》一书中,时任公司总裁的罗伊·瓦杰洛斯
(Roy Vagelos)博士写道:“太多的(艾滋病)患者正在死去,疾病正在蔓延,受感染的人群正在发生变化。……默沙东新药研
究院从上到下对艾滋病毒研究的专注以及公司对这个项目的投入之多都是难以置信的,尽管我们始终面临着彻底失败的威胁。”
[5]
这里当然有科学家对探索未知的好奇以及医药工作者征服疾病
的欲望,但同时也充分显示了制药公司及其员工以人为本、救死
扶伤的高度责任感和应尽的义务。艾滋病威胁着整个人类的健
康,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控制它的蔓延,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1989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科学家首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了艾滋病毒蛋白酶(HIV protease)的三维晶体结构,随后由美国
国立健康研究院(简称NIH)精细化,为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的研发奠定了基础。1993年,默沙东实验室成功地合
成了高效、高选择性的蛋白酶抑制剂——佳息患(Crixivan),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FDA)递交了新药申请(New
Drug Application,简称NDA),开始了佳息患的临床试验。同
年,为了攻克艾滋病,默沙东制药和14家制药公司联手,宣布成
立跨公司的合作,交换信息,共享资源,并尝试新药的组合治
疗。1995年,临床三期的结果显示,服用佳息患能有效地
(99%)降低血液中的艾滋病毒,与其他抗病毒药物联合服用
时,效果更加明显,可以把艾滋病毒降到检测极限以下。1996年
3月13日,继罗氏制药的沙奎纳韦(Saquinavir,1995年12月6日)
和雅培制药的利托那韦(Ritonivir,1996年3月1日)之后,默沙
东制药的佳息患作为第三种HIV蛋白酶抑制剂的新药上市,迅速
扭转了艾滋病无药可救的局面,死亡率大大降低,在很大程度上
消除了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慌。
佳息患虽然是第三种上市的HIV蛋白酶抑制剂,但它绝不是
一种仿制专利药(Me too drug),而是一种更优专利药(Me
better drug),受到医生和患者的一致好评,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
后来居上,全球的年销售额达到7亿多美元,超过了前两种HIV蛋
白酶抑制剂药物,占当时市场份额的40%。佳息患的成功不仅打
破了市场和财务部门当初对抗艾滋病新药的预测,扭亏为盈,为
公司创造了相当的利润,而且应验了乔治·默克先生60多年前的预
言:如果我们能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新药,帮助他们恢复健
康,利润就一定会随之而来。兵不解甲
佳息患等HIV蛋白酶抑制剂的成功,极大地提高了制药行业
征服艾滋病的信心。默沙东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兵不解甲,继续积
极寻找治疗艾滋病的新途径。
在学术界和制药业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对艾滋病毒及其感染
和传播途径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除了HIV蛋白酶之外,我们又找
到了HIV逆转录酶(HIV reverse transcriptase,简称RT)和HIV整
合酶(HIV integrase)等新的靶标。艾滋病毒属于逆转录RNA病
毒,而HIV逆转录酶则是一类存在于部分RNA病毒中能以单链
RNA为模板合成DNA的酶,HIV整合酶则是帮助逆转录病毒把携
带病毒遗传信息的RNA整合到宿主细胞的酶,它们在艾滋病毒感
染(入侵宿主细胞)过程中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说起RNA逆转录酶的发现,这可是现代分子生物学中一个很
重要的里程碑,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学术界关于生命起源于DNA
的学说。回到20世纪7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中心法则(Central
dogma)仍旧是:生命的信息先是从DNA转录到RNA,然后再从
RNA转化为功能和结构性的蛋白质。但是两位年轻的美国生物学
家——威斯康星大学的霍华德·特尔明(Howard Temin)和麻省
理工学院的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的新发现颠覆
了这个被学术界普遍接受的学说,他们分别独立发现的RNA逆转
录酶可以将RNA分子所携带的遗传信息反转录到DNA分子里,揭
开了RNA病毒感染之谜。1975年,特尔明和巴尔的摩共享了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后不久,耶鲁大学的西德尼·奥尔特曼
(Sidney Altman)和科罗拉多大学的托马斯·切赫(Thomas
Cech)又分别发现了具有催化功能的RNA分子——核酶
(Ribozymes),共享了1989年诺贝尔化学奖。由于这两项重要
的发现,原先被边缘化的有关生命起源的“RNA世界假说”逐渐成
为学术界的主流:最早的生命形式很可能仅仅依靠RNA来存储遗
传信息和催化化学反应,并以此完成自我复制。因为RNA逆转录酶由病毒自身携带,并且不存在于宿主细胞
内,所以它可以作为抗病毒药物的合适靶标。1998年9月,在佳
息患上市仅两年半之后,默沙东的依非韦仑(Efavirenz)就成功
地被FDA鉴定通过,成为首个上市的非核苷类HIV逆转录酶抑制
剂药物,为治疗艾滋病提供了新的手段,也为高效的“鸡尾酒”抗
病毒复方药物治疗奠定了基础。
默沙东的抗艾努力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他们锁定了下一个
靶标:HIV整合酶,一场新的攻坚战打响了。
整合酶志在必得
前面提到过,HIV整合酶是帮助逆转录病毒把携带病毒遗传
信息的RNA整合到宿主细胞的酶,它在艾滋病毒感染过程中也起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整个制药界早期所有寻找HIV整合酶
抑制剂的先导化合物的努力都没有成功,先后都放弃了HIV整合
酶抑制剂项目。制药巨头辉瑞公司的科学家在2007年还发表了一
篇论文,计算并论证了为什么他们认为HIV整合酶是最不可能成
药的靶标。
尽管默沙东实验室的研发团队也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但是大
家没有轻言放弃,彰显了“舍我其谁”的豪迈。在经历了数次失败
之后,他们终于跨过了第一道“门槛”,发现了先导化合物,药物
设计有了一个初始的模板。在注意到了流感病毒的内切核酸酶
(Endonuclease)和HIV整合酶之间在生物化学方面的相似性之
后,默沙东的病毒学专家团队建立起了酶学筛选平台,有效模仿
病毒RNA的整合过程,然后从公司的化合物库里精心挑选了几百
个内切核酸酶的抑制剂进行筛选。他们不仅发现了一些能抑制核
酸链整合转录过程的二酮酸衍生物,而且这些二酮酸的衍生物在
细胞培养中也能相当有效地抑制HIV的复制,这在当时是从零到
一的关键性突破。
但是二酮酸衍生物不是理想的先导化合物,它们的化学稳定性不好,能与金属离子螯合,还有生物反应活性,用现在的术语
叫“缺乏类药性”(Lack of drug-like properties),公司内部也存有
不少怀疑的声音。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默沙东的药物化学
团队硬着头皮向前推进,竟然再次杀出重围,又开创出了一片新
天地。他们建立了有规律可循的构效关系,提高了先导化合物抗
病毒的抑制活性,而且还找到了能取代关键药效基团二酮酸的等
效基团,大大提高了“类药性”。
打开局面之后,他们很快就找到了第一个临床候选药物,进
入了更加艰难、投入资源更多的临床开发阶段。一而再,再而
三,默沙东的前三种HIV整合酶抑制剂临床候选药物都出现了这
样或那样的问题,被先后叫停。研发团队根据临床试验的信息反
馈,不断修正药物设计,完善化合物的体内外性质,终于将第四
种临床候选药推过了最后一道“门槛”。
2007年10月,默沙东新药艾生特(Isentress)通过了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鉴定,成为第一个上市的HIV整合酶抑制
剂。更重要的是,2011年12月艾生特被进一步批准用于年龄2~
18岁的人群的治疗,[6]
给未成年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以人为本
目前,对艾滋病毒的有效控制很大程度上仍旧局限于医疗条
件好的发达国家,因为在那里,患者有条件享受社会医保或购买
私人医保,可以严格地根据医嘱用药。但是在许多亚非拉发展中
国家,艾滋病还在继续蔓延,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统计,仅
2005年一年,艾滋病就夺去了300多万人的生命,其中约60万是
儿童。2012年,全球范围内被艾滋病毒感染的人群已高达3500万
人,主要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
[7]
在中国,被艾
滋病毒感染的人群总数虽然不多,但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上升趋
势,到2008年,艾滋病已成为导致中国人死亡人数最高的感染性
疾病。中国的医务人员必须努力提高民众对艾滋病的认识,积极地控制艾滋病毒的进一步扩散。
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患者和政府大都无钱购买西方大药厂
(Big Pharma)的抗病毒新药。尽管一颗胶囊或是一粒药片的成
本只有几毛钱,但药厂在研发过程中的投入却是天文数字,根据
最新的统计数据,开发一种新药的耗资超过10亿美元。所以,在
制定药价时,大药厂必须考虑其专利保护的年限以及市场的需
求,以期收回成本并有盈余。最后的药价与药片的生产成本基本
上是无关的,只有这样,制药公司才有实力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
入新药研发,我们才有希望攻克那些还在威胁人类健康的癌症和
其他疾病。然而,社会舆论却不这么看,时常一味地指责大药厂
为了追求利润“见死不救”,眼看着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人挣扎在
痛苦和绝望之中。面对这个两难的现实,默沙东制药再一次以人
为本,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合作,努力把佳息患送到非洲国家患者
的手中。早在2000年,默沙东就开始与博茨瓦纳政府联系,大幅
度降低药价,然后通过美国政府、当地政府、世界银行、国际货
币基金会(IMF)和各大私人基金会(如盖茨基金会),将佳息
患等抗艾滋病药物分发到非洲国家。
2001年,默沙东制药还率先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大幅
度降低抗艾滋病药物的价格,为整个人类的健康事业承担了应尽
的责任和义务。2005年,默沙东基金会
[8]
与中国卫生部签署了
全面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合作项目,并结成抗艾滋病合作伙伴关
系(China-MSD HIVAIDS Partnership,简称C-MAP),向中国
提供首期5年、共计300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偏远地区艾滋病的
预防与治疗。“关艾计划”响应卫生部的艾滋病防控策略,深入推
广“治疗与预防同步”的理念,及时更新一线艾滋病医生的诊疗知
识,更好地为患者提供治疗和关怀。经过多年的努力,C-MAP项
目在提高一般大众对艾滋病的认知,提升政府卫生机构防治能
力,加强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关怀,降低疾病对社区产生的社会和
经济影响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荣获了2011年中国民政
部颁发的第六届“中华慈善奖”
[9]
,被誉为“最有影响力的慈善项
目”。每一个药物分子的价值可以用它的年销售额来估算,但它对人类健康的贡献却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制药工业救死扶伤,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崇高产业,也正因
此,和其他产业相比,它始终处于道德标准的显微镜下,容不得
半点“忽悠”。造假药、卖假药天理难容;研发了新药之后漫天要
价、见死不救,同样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中国的新药研发产
业来势迅猛,投入之多、涉及面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快
速发展的过程中,希望中国制药界能以史为鉴,坚持以人为本,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2011年3月初稿于上海
2017年6月修改稿于新泽西第二章 人类与细菌的“军备竞赛”
从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到新型复合抗生素的研发
1942年3月14日,一个被细菌感染的病人接受了美国历史上
第一例青霉素治疗。光这一个病人就用掉了全美国当时青霉素库
存的一半,而生产这些非常难得的少量青霉素的厂家就是美国默
沙东制药的前身,当年的默克制药公司。
青霉素:从弗莱明的偶然发现到默沙东的大规模生产
青霉素(Penicillin)的发现是人类生存和致病细菌(又称病
原菌)的长期斗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928年9月28日,英国伦敦大学圣玛莉医学院(现属伦敦帝
国学院)细菌学教授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实
验楼的地下室里发现,他前几天忘了加盖子的细菌培养器皿中,长出了一种蓝绿(青)色的霉菌,而在这些蓝绿色的霉菌孢子的
周围,细菌的生长被抑制住了,形成了一个无菌的圆环。弗莱明
教授敏锐地判断出这些蓝绿色的霉菌孢子里一定含有某种抑制细
菌生长的化学物质,他将其称为“青霉素”。
这个很偶然的发现引起了细菌学家们的关注,但是由于没有
实用的生产线路,包括弗莱明教授本人对青霉素的研究都曾一度
中断。直到1938年,由英国牛津大学的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恩斯特·伯利斯·钱恩(Ernst Boris Chain)和诺曼·希特
利(Norman Heatley)领导的团队成功地从青霉菌里提炼出了抗
菌的化学物质——青霉素,才使得这一重要的发现造福于人类。
为此,弗莱明、钱恩和弗洛里共同获得了194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于青霉素比当时的磺胺类药物更加安全有效,马上获
得了整个医药界的热切关注。但是,青霉素的进一步研发却遇到
了很大的困难,除了实验室的小试之外,连车间中试都未能取得
成功,更不用说大规模生产了。当时的一位资深行家是这样进行
描述的:“那些该死的霉菌就像是一个坏脾气的歌剧演员,令人
难以捉摸,产率非常低,分离极为困难,提取更是要命,纯化简
直是灾难性的,测试也不可能令人满意。”这可不仅仅是他一个
人的看法,整个制药界都对青霉素的工业化生产一筹莫展。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
大战。到了1942年3月,由默沙东生产的全美国的青霉素库存仅
够治疗两个病人,根本无法满足前线伤员救护的紧急需要。在美
国政府的组织下,默沙东与美国几大制药公司结为同盟,精诚合
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共同攻克了青霉素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这一
难题。默沙东制药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浸润式深罐发酵方法
(Submerged deep tank fermentation),大大提高了青霉素的产
率。1943年,默沙东制药新建成的青霉素车间共生产了42亿个单
位的青霉素。1945年,默沙东青霉素的年产量迅速增长到了6400
多亿个单位,满足了当时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大战场以及
美国国内的需求。青霉素的广泛和及时使用,大大降低了伤员的
感染,加快了伤口的愈合,减少了因伤口感染而不得不进行的截
肢和相关手术,使盟军的非战斗减员降低了10%~15%,对反法
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33年时仅有35人
的默沙东新药研究院(当时名为Merck Institute for Therapeutic
Research)也发展为战后拥有500多名研究人员的大型研究机构,为战后现代化制药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链霉素:从“土壤之人”威克斯曼到默沙东的专利和技术转让
在青霉素被发现之前,细菌感染让人谈虎色变。肢体上一个
小小的创伤经常会因为感染而不能愈合,最后只能截肢,如果不
及时的话,很有可能会夺去患者的生命。细菌的历史比人类长很多,它们是这颗星球上的老住户了,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有细菌的“亲密陪伴”。但是,在农业文明
之前,人类与细菌基本上还是能“和平共处”的,那时我们的祖先
以狩猎、采集和游牧为生,无定居地,人口密度很低,零星的细
菌感染不可能有机会大面积地快速传播。农耕把我们的祖先牢牢
地拴在了土地上,谷物和牲畜的驯化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定居的
村落逐渐发展到集镇,人口密度越来越高,先前零星的细菌感染
在高密度的人群集居地有了广泛传播的可能性,再碰上传染性强
的细菌,就会发展成可怕的“瘟疫”,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整个村
落变成坟场,哀鸿遍野。早在公元前430年前后,就爆发过人类
历史上著名的“雅典大瘟疫”,持续了近4年,导致近半数的希腊
人惨死,几乎摧毁了希腊城邦。
因为细菌是微小的单细胞生物,用肉眼无法看见,所以人类
长期以来一直被这些看不见的小东西所困扰,把“瘟疫”视为“妖魔
作祟”或是“上帝惩罚”。直到1683年,荷兰科学家列文虎克使用自
己设计的单透镜显微镜,在放大了约200倍之后,第一次观察到
了这些“活的小东西”(所以叫微生物),科学家们开始怀疑,就
是这些“活的小东西”给人类带来了疾病和瘟疫。其后的几百年
里,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直接或间接地把“传染性疾病”的起因与
这些微生物联系在一起,把它们称为“细菌”(Bacteria)。19世纪
末,著名的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罗伯特·科
赫(Robert Koch)确定无疑地证实了细菌可以导致疾病。到了20
世纪初,寻找抑制和杀死致病细菌的方法和药物已经成了医药研
究的大热门。
1938年,默沙东制药为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教授塞尔曼·威克
斯曼(Selman Waksman)的实验室设立了学术基金,用于土壤微
生物学(Soil microbiology)的研究。土壤微生物学在当时还是一
门新兴的学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得不到足够的科研经
费。默沙东制药公司的及时投入,使得威克斯曼教授的研究可以
顺利进行。1940年,威克斯曼教授的研究团队首先发现了放线菌
素(Actinomycin),根据默沙东与罗格斯大学以及威克斯曼教授三方的合同,罗格斯大学科研基金会将威克斯曼教授的放线菌素
发明专利转让给默沙东制药,由默沙东制药独家研发,于1964年
上市。威克斯曼教授最先把这一类化合物称为“抗生
素”(Antibiotics),这个名词很快被学术界接受,并在社会上流
传开来,成为最常用的医药名词之一,妇孺皆知。
威克斯曼教授毕生从事土壤微生物学的研究,从他的实验室
里先后发现了20多个新型抗生素,其中最著名的是1943年发现的
链霉素(Streptomycin)。链霉素的问世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因为那是当时唯一能治疗肺结核(Tuberculosis)的抗生素,威克
斯曼教授不但因此而荣获195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且还
成了《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被誉为“土壤之人”(Man of the
Soil)。
和放线菌素一样,链霉素的发明专利也归默沙东制药公司所
拥有,它理所当然地成为链霉素的独家生产者。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肺结核在很多国家开始流行,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默沙东生产的链霉素被视为“救命稻草”,给患者带来了希望,同
时也给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是,在世界范围内,链霉素供
不应求,肺结核仍在继续蔓延,在威克斯曼教授的请求下,乔治·
默克毅然决定将链霉素的专利权退还给罗格斯大学科研基金会,这样一来,其他制药公司也可以从罗格斯大学获得许可,生产和
销售链霉素,共同抑制结核菌的蔓延。战败的日本是当时肺结核
流行最严重的国家,默沙东制药把自己的链霉素生产技术传授给
了日本人,为日本战后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虽然默沙东制药
在链霉素的专利授权和技术转让中没有赚一分钱,但后来的发展
却让默沙东制药声名鹊起,成为最受尊敬的制药公司之一。许多
健康医药领域的企事业都乐意与默沙东公司合作,他们看重的是
默沙东公司以人为本、不贪图眼前利益的企业价值观。
抗药性:从进化论之必然到人类健康的新威胁
青霉素、链霉素等多个天然抗生素的发现,使人类在与细菌的“军备竞赛”中取得了显著的优势,细菌感染大多能很快被控制
住,不再令人谈虎色变。但好景不长,这个优势是短暂的,人类
刚刚从传染病和瘟疫的阴影里走出来,稍稍喘了一口气,细菌对
这些抗生素的反击战就已经初见成效——具有抗药性的变异细菌
被发现了。
抗药性或耐药性(Drug resistance)是指药物治疗疾病或改善
病人症状的效力降低。尽管抗药的细菌给人类健康带来了新的威
胁,但这也是进化论的有力佐证。
很多人以为抗药性是因为细菌对抗生素产生了某种针对性变
异,其实这是不准确的。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有物种都在持
续不断地随机变异,在生存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一个物种内
因为随机变异而产生的不同基因类型的分布也相对稳定,呈“动
态平衡”,最适应外部环境的基因类型总是在数量上占绝对优
势,被看作“正常”物种,而其他相对劣势的基因类型则被看作“变
异”物种。一旦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近年来的气候变化,一个物种内能耐热耐旱的基因类型相对于其他的基因类型就有了
优势,哪怕一开始只有一丁点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能耐热
耐旱的基因类型在此物种里所占的比例就会越来越多,逐渐
被“富集”起来。如果气候变化再持续下去,它最终会成为占绝对
优势的“正常”物种,这就是达尔文所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
存”。一个物种能不能在逐渐变暖的地球上生存下来,取决于这
个物种内随机变异的基数是不是足够大,基因类型的分布是不是
足够广。如果基数太小,分布不广,能耐热耐旱的基因类型不存
在或者是达不到“可持续密度”,那么这个物种迟早会被淘汰的。
当一个物种,比如大熊猫,数量下降到一个临界值,它的基因类
型分布就会十分有限,对于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就会很差,这就
是“濒危物种”所面临的困境。
细菌不是濒危物种,虽然抗生素的广泛使用给这些小东西的
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但是细菌的基数足够大,基因的分布极
广,而且各种变异的出现又非常快,绝不是几个抗生素就能斩尽杀绝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青霉素使用之前,对青霉素有抵抗力
的细菌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在没有使用青霉素所带来的“自然选
择”压力的生存环境中,它们的优势不能体现出来,只能维持
在“劣势物种”的低水平。青霉素来了,给没有抵抗力的“正常”细
菌带来了灭顶之灾,但是极少数有抵抗力的“劣势”细菌活了下
来,并且把这种耐药特性遗传给了它们的后代,产生了有抗药性
的“变异细菌”。一代又一代,随机的变异不断地发生着,在抗生
素的巨大压力之下,不具有抗药性变异的细菌被无情地淘汰了,而大部分能产生抗药性的变异则“被选择”了。它们不断繁衍,抗
药性越强的基因类型越是容易“被选择”,所谓的“抗药性”也就越
来越强,给人类的生存和医药工作者带来了新的挑战。
根据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研究人员的最新报道,[10]
目
前仅在欧盟以及欧洲经济区(EUEEA),每年因为抗药性细菌
感染而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3.3万,与此相关的医疗费用至少达
15亿欧元。2013年,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在《抗药性威胁》
的报告中称,美国每年因抗药性细菌感染而患病的人数超过200
万,其中至少有2.3万人死亡,与其相关的直接医疗保健费用估计
高达200亿美元,社会生产力损失更是高达350亿美元。在人口众
多的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无可靠的统计数据,但是
不难想象,在发展中国家里抗药性细菌性感染所造成的死亡人数
应该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全球抗生素研究与发展伙伴(The
Global Antibiotic Research Development Partnership,简称
GARDP)2018年9月发布新闻称,在全球范围内,每年因抗药性
细菌感染而造成的新生儿死亡人数就超过20万。如何在全球范围
内有效控制抗药性细菌感染,是一项刻不容缓的艰巨任务。
碳青霉烯:从细菌抗药性的机制到默沙东的新型抗生素
细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目前已知的主要有4种机制:
1.最常见的是,细菌把入侵的抗生素分解掉,比如耐药菌产生的β-内酰胺酶(β-lactamase)能分解包括青霉素在内的β-内酰
胺类抗生素的β-内酰胺环;另外,耐药菌产生的钝化酶(磷酸转
移酶、核酸转移酶、乙酰转移酶)可以使氨基糖苷类的抗生素失
去抗菌活性。
2.细菌自身发生的突变使得抗生素的作用靶点(如核酸或核
蛋白)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抗菌药物就无法或不易发挥作用,比
如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就是产生了青霉素的蛋白结合部
位的某些变异,降低了药物的活性。
3.细菌细胞膜渗透性或其他特性发生变异,使抗菌药物无法
进入其细胞内。
4.细菌的基因突变产生的外排泵系统(Efflux pumps),以主
动运输的方式将进入其细胞内的药物排出细胞外。
以分解青霉素的β-内酰胺酶为例,早期发现的内酰胺酶效率
很低,并不能很有效地分解青霉素,所以这些早期的抗药细菌在
青霉素压力下的存活率比“正常”细菌仅仅高了一点点。这些“一点
点”的随机变异在青霉素“自然选择”的压力下不断地被富集,被“优化”,直至产生高效率的内酰胺酶。为了制服这些能产生β-
内酰胺酶的抗药细菌,医药界的科研人员开始寻找不会被β-内酰
胺酶分解的新型抗生素,由默沙东制药研发的亚胺培南
(Imipenem)就是其中很成功的新一代“碳青霉
烯”(Carbapenem)类抗生素。
从概念上讲,研发耐β-内酰胺酶的新型抗生素不会很难,但
各大药厂的早期尝试都没有获得成功。“人算不如天算”,1976
年,当各大药企的研究人员还在不断摸索,到处碰壁的时候,默
沙东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从一种链霉菌的发酵液里发现了一个新型
的天然抗生素——噻烯霉素(Thienamycin),因为化学稳定性很
差,噻烯霉素的结构到1979年才被确定。科学家们发现它与青霉
素很相似,也含有β-内酰胺的核心结构,但是内酰胺并环上的硫
原子被碳原子取代了,另外还加进了碳碳双(烯)键,所以它被定义为“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这些结构上的变化使得碳青霉烯很
难被β-内酰胺酶分解,但保留了青霉素广谱杀菌的特性,正是医
药界苦苦寻找的新一代抗生素。从进化论角度看,碳青霉烯类抗
生素应该和有抗药性的细菌一样,也早就存在了,但从筛选技术
上讲,只有在抗药性的细菌被“选择和富集”了之后,能够杀死这
些细菌变异的天然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才有可能被发现,因为它们
反过来又被这些新型的耐药细菌“选择”了。
噻烯霉素本身的化学稳定性不好,不易于制备和保存,也不
适合于临床应用。但是,有了这个样板,“仿制”起来就容易多
了,而且目标也明确,那就是要发明一个比噻烯霉素更稳定,适
合于临床使用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通过一个很简单的化学修
饰,将噻烯霉素支链上的氨基保护起来,默沙东的科研团队合成
出了亚胺培南——第一个被批准用于临床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从此,人类与细菌的“军备竞赛”进入了一个新的轮次。
愈演愈烈:从“超级细菌”的发现到“后抗生素时代”
这一次,我们学乖了。我们无法阻止抗药性的出现,但是我
们可以延缓它的发生,延长抗生素的使用期。为了延缓针对碳青
霉烯有抗药性的细菌变异被选择和富集,发达国家对这些新型抗
生素的使用做了非常严格的控制,剂量与服用期必须严格遵守医
嘱,以保证其疗效,尽量避免滥用和误用。
但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医药管理制度不健全,缺
乏基础的医学常识教育,滥用抗生素的现象非常严重。到目前为
止,还有很多中国老百姓,不管是什么病,只要有头疼脑热,先
吃几片头孢(头孢菌素[Cephalosporin],另一种β-内酰胺类的
抗菌素)再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出现人们常说的“药吃多了,不管用了”。中国抗生素滥用的状况到底有多严重?中国药学会
发布的《2009—2011年抗菌药临床使用情况初步分析》显示,在
其样本医院中,抗菌药物占医院药品总金额的年平均份额为19.3%,远远高于国际一般水平。
早早晚晚,在多种抗生素的持续压力下,超级细菌还是跟我
们面对面了。
超级细菌并不是单纯地指某一种细菌,人们一般把对几乎所
有抗生素有抗药性的细菌统称为超级细菌,包括多重耐药铜绿假
单细胞菌、多重耐药结核杆菌、泛耐药肺炎杆菌、泛耐药绿脓杆
菌等。这个大家族的成员还在不断地被发现,并且越来越多。在
众多的超级细菌中,最著名的要数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名字太长,大家就把它简称为MRSA。最早的时候,青霉素
就能轻松搞定这种细菌,可随着抗生素的普及,没有抗药性的金
黄色葡萄球菌都被杀死了,剩下的都是有抵抗力的变异物种,能
产生青霉素酶破坏青霉素的药力。发展到今天,唯一有机会对抗
MRSA的只有万古霉素(Vancomycin)了。
后来,科学家们又在一些曾在印度接受过外科手术的病人身
上发现了一种含有金属β-内酰胺酶的超级细菌,这种细菌被命名
为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1(New Delhi metallo-β-lactamase-1,简
称NDM-1),它与以往的耐药菌有很大的不同,复制能力很强,传播速度快且容易出现基因突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超级细菌,因此它的出现引起了医药界的高度关注。
2015年底,在一篇没有多少国人注意的科学论文中,华南农
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宣布从中国的细菌里发现了一种正在传播的基
因,取名为MCR-1,使它们能够抵抗现有的最强大的常常是作
为“最后手段”的抗生素。中国长期以来人口众多而又密集,人畜
之间的近距离接触相对频繁,这使中国成为新的感染性疾病的滋
生地。目前中国牲畜抗生素的用量(每头)是美国的三倍,占全
国抗生素消耗总量的一半。据信,最新发现的耐药基因就是在中
国的家猪中变异产生的。有证据显示,含有这种基因的耐药细菌
已蔓延到了老挝和马来西亚。
有科学家表示,一旦某种超级细菌在全球蔓延开来,人类将进入“后抗生素时代”。
所谓“后抗生素灾难”(Post-antibiotic apocalypse)指的是“泛
耐药性”超级细菌的普遍出现使得抗生素不再有效,感染性疾病
再次成为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这个说法许多年前就有人提出
了,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很多人的脑子里已经淡漠
了。其实它正在悄悄地降临,而中国极有可能是后抗生素时代的
主战场之一。很多微生物学家表示,目前的情况看起来非常不
妙,我们正在这场战争中失去阵地,所有的祸源都已各就各位,NDM-1、MRC-1等耐药基因在全球的蔓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也
许就是今年、明年或后年。
面对这场渐渐逼近的“后抗生素灾难”,制药人应该有怎样的
担当?
论持久战:制药人肩负重任
你也许会问,既然具有抗药性的细菌始终存在,与用不用抗
生素无关,为什么滥用抗生素会恶化抗药性的问题?这主要是一
个轮次的问题,细菌每隔几小时就繁殖一代,使用抗生素越频
繁,细菌被选择的轮次也就越多,抗药变异的富集也就越快,所
谓的“抗药性”就越强。
另外,严格控制抗生素的使用,还能使已经有抗药性的细菌
自动退化,失去抗药性。在抗生素的压力下,不含有NDM-1、MRC-1等耐药基因的细菌是劣势物种,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一
旦它们生存的外部抗生素压力消失,就能反客为主,重新成为优
势物种,而那些能产生β-内酰胺酶的耐药性细菌就没有了优势,原来是生存的必需,现在却成了消耗能源的累赘,它们反而成了
劣势物种,失去了竞争力,繁衍几代之后就被边缘化了,回到先
前的以不耐药细菌为主的自然分布。这有点像超级大国军备竞赛
中的“裁军谈判”,双方销毁核武器,回到常规武器,因为维持一
个时刻准备着的庞大核武器库是很消耗资源的。可见抗生素的使用是很有讲究的,要规范化。什么情况下
用,用多少,用多长时间,都应该严格遵照医嘱。目前默沙东制
药正积极协助中国相关专业协会,支持中国更加规范地使用抗生
素。
亚胺培南的上市使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研发成为医药界的一
大热门。为了提高亚胺培南在人体内的半衰期,延长药效,默沙
东又推出了亚胺培南与西司他丁(Cilastatin)的复合抗生素——
泰能(Tienam)。作为对付抗药性很强的“超级细菌”的重要手
段,泰能是经验性治疗(医)院中重度感染的一线用药。2001
年,默沙东又推出了新一代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怡万之
(Invanz,学名厄它培南[Ertapenem]),为制服“超级细菌”提
供了新的武器。
变异自始至终存在,进化永远不会停止。
无论是“军备竞赛”还是“裁军谈判”,人类与致病细菌之间的
战争均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持久战”。为了人类的健康事业,医
药领域的科研人员始终活跃在抗生素研发的第一线,为人类的健
康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12年12月初稿于上海
2017年7月修改稿于新泽西第三章 为了一个没有河盲症的世界
从伊维菌素谈以人为本的新药研发
在默沙东研发的众多新药里,抗寄生虫病的伊维菌素
(Ivermectin)是颇具传奇色彩的。
根据默沙东实验室老前辈威廉·C.坎贝尔(William C.
Campbell)博士的回忆:“在一个特殊的日子,1975年5月9日,一
间实验室的鼠笼里有一只老鼠被特意感染了蠕虫——但不足以致
病。那一天,它的食物有些变化——一些液体被掺进了它的常规
食物中。这只老鼠吃了近一个星期的特殊食物,然后恢复正常饮
食。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它体内的蠕虫就不见了!”
[11]
获奖感言:抗寄生虫药荣登大雅之堂
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美国默沙东实验室生
物学家坎贝尔、日本微生物学家大村智以及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表彰他们对发现抗寄生虫药物伊维菌素和青蒿素所做出的重要贡
献。
因为我写过有关伊维菌素的研发故事,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公布之后的几天,我收到了不少询问的微信、电话和邮件,都
是问坎贝尔博士的。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坎贝尔博士不但是我
在默沙东的老前辈,而且也是我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学长,我挺自
豪的。只有一位女士在电话里弱弱地追问了一句:“那么那个日
本人是干什么的?”我说那位日本老先生就是一个“挖烂污泥的”。
她惊讶地说:“挖烂污泥也能得诺贝尔奖啊!”我们都笑了。虽然是句玩笑话,但是那个排在屠呦呦和坎贝尔之间,中国
人很少提及的大村智先生一辈子收集和研究土壤样品却是一点不
假,他本人在题为“土地的华丽馈赠”的获奖感言中就展示了他收
集土壤样品时的照片。
[12]
其实,大村智不是因研究“烂污泥”而
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一人,著名的链霉素发现人、1952年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威克斯曼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土壤之人”。 [13]
大村智先生在他的获奖感言中说道:“世界上最重要的、革
命性的、用途广泛的,但相对而言仍旧不出名的药物之一起源于
日本的土壤里,无论从字面上看还是从含义里讲皆是如此。伊维
菌素,一种衍生自单个微生物的药物,每年有超过2.5亿人(是全
日本人口的两倍)可免费获得,就发现于日本的土壤里。它对于
改善数亿男子、妇女和儿童(主要是贫穷和贫困社区)的总体健
康和福利的影响依然是无法比拟的。它打破了许多先入为主的陈
旧观念,尽管这个单一疗法多年来被广泛持续地使用,但耐药性
并未发展。这促使它被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药物清单’,这
是所有基本卫生系统中最重要的药物汇编。一些国际公共卫生专
家也大力推荐,将伊维菌素作为一种简单预防和有效治疗的公共
卫生干预措施,在寄生虫多发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规模地推
广。”
“简而言之,伊维菌素被证明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生物医学发
现之一……对全世界的动物和人类健康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有益影
响。”
伊维菌素:匪夷所思的抗寄生虫药
20世纪70年代初,默沙东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与世界各地的研
究机构合作,收集各种土壤样品,从中培养、筛选和寻找抗微生
物的活性物质。结果,在收集到的4万多个土壤样品里,仅在一
个土壤样品的培养和筛选过程中,发现了一类全新的抗寄生虫的
化合物。这个唯一的土壤样品是大村智所在的日本东京北里研究所提供的,它来自静冈地区伊藤市,是川奈海滨的高尔夫球俱乐
部附近收集的单一土壤样品。
这些样品在被送到默沙东实验室之前,大村智在北里研究所
的团队已经对它们进行了初步的筛选,并没有发现什么有意义的
东西,所以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在默沙东实验室的一个实验
员将这些土壤样品的培养液用于一些常见的寄生虫时,奇迹出现
了。他发现其中一个样品把所有的寄生虫杀得一干二净,欣喜之
余,他从盛满培养液的烧瓶中取出几滴,放到另一个烧瓶里大量
稀释之后,再用于那些寄生虫,结果还是把所有的寄生虫杀得一
干二净。实验人员将这个已经稀释过的培养液又稀释了一次,得
到的杀虫效果仍旧是一样的。由欣喜转为惊讶,这个实验人员连
续将培养液的稀释过程重复了好几次之后,发现它还是有很强的
杀虫效果。他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筛选的团队,经过几次重复之
后,大家确信无疑,这个培养液里一定存在着一些非常高效的抗
寄生虫的化学物质,他们决定做动物实验,于是故事开头坎贝尔
博士回忆的那一幕出现了。
通过对该菌种的培养、发酵、分离和纯化,默沙东实验室的
研究人员找到了这些化学物质,将它们命名为阿维菌素
(Avermectin)。阿维菌素是一些含糖的大环状内脂类有机化合
物,这个家族的不同成员对不同寄生虫的杀虫效果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化学稳定性也有明显差别,不是很理想。在深入研究的过
程中,默沙东实验室药物化学部的研究人员把阿维菌素家族的一
员——阿维菌素-B1(Avermectin-B1)的一个碳碳双键(C22
=C23 )通过均相催化加氢还原,一步化学反应就做成了一个集中
了阿维菌素家族不同成员优点的新化合物,不但稳定性好,而且
生物利用度也有提高,它就是伊维菌素。
伊维菌素是第一个“体内外杀虫剂”(Endectocide),既能杀
死体内寄生虫,也能杀死体外寄生虫。它的抗寄生虫药性之强实
属罕见,比如,每千克体重0.001毫克的口服剂量就足以杀死狗体
内的幼年心脏蠕虫(Dirolilaria immitis,又名Heart worm),即使对于伊维菌素不太敏感的牛食道口线虫(Oesophagostomum
radiatum)和牛肺蠕虫(Dictyocaulus viviparus),每千克体重
0.05毫克的口服剂量也就够了。相比之下,其他口服药物的用量
在每千克体重40毫克以上。伊维菌素的适用面也很广,能有效地
杀死线蠕虫、跳蚤、虱子等寄生虫,每月一次用药几微克就可以
有效地防止心脏蠕虫对狗的侵害。
寄生虫病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人群里已经很少见了,但在欧美
的畜牧业和宠物业,每年因寄生虫病而造成的商业损失不下40亿
美元。兽用的伊维菌素上市之后,很快成为家畜和宠物抗寄生虫
的理想用药,年销售额接近10亿美元,北里研究所也因此获得了
可观的提成。最初的菌种经发酵后,每立升培养液只能产生大约
9微克的阿维菌素,经过工艺部门的不断筛选和优化,新菌种发
酵后阿维菌素的产量提高了五六个数量级。多年来,只有默沙东
拥有能产生阿维菌素的唯一菌种,直到1999年,意大利的一家实
验室才找到了第二个能产生阿维菌素的菌种,结束了默沙东对它
的垄断。
河盲症:令人生畏的寄生虫病
在人口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里,各种各样的寄生虫病,如热
带的疟疾、血吸虫病等,依然严重地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在撒哈
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里,有一种令人生畏的寄生虫病,因为多
发于居住在河边的人群,而且会导致患者失明,被称为“河盲
症”(River blindness)。
在水源奇缺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部落民族一般都沿河而
居,以利生息、农耕和放牧。然而,在那一带的河水里繁殖的黑
蝇大多携带着一种被称为“盘尾丝虫”(Onchocerca volvlus)的寄
生虫蚴。在河边作息的人被黑蝇叮咬后,盘尾丝虫蚴便被注入体
内,开始了在人体内的寄生周期。虫蚴在患者的皮下慢慢地长
大,最长的成虫可达两尺。它们聚集于皮下,使患者奇痒无比。
成虫一旦进入患者的眼睛,就会引起角膜的炎症,最终导致失明。在一些发病严重的村落里,50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失明的患者
甚至高达60%。
在研发伊维菌素的过程中,默沙东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注意到
了伊维菌素可以有效地杀死一种与盘尾丝虫很类似的马的寄生
虫,进而敏锐地推断出伊维菌素也许能杀死盘尾丝虫,从而治愈
河盲症。
[14]
他们很快拟订了进一步研究的方案,递交给了当时
主管研发的公司副总裁罗伊·瓦杰洛斯博士。单从账面上看,这又
是一桩赔本的买卖。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集中了世界上最贫困的
国家,生活条件之恶劣、物质资源之匮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研发成本甚高的各大制药公司不可能在那个地区获得任何的利
润。但是,为了坚持以人为本,默沙东公司还是决定做这桩赔本
的买卖。带着探索未知的好奇和征服疾病的强烈欲望,带着救死
扶伤的责任和义务,默沙东实验室的科学家远赴非洲,首先在塞
内加尔开始了小规模的安全评估(Safety assessment,简称安评)
与临床试验,结果非常令人鼓舞,试验也很快扩大到马里、加
纳、利比里亚、乍得等国。伊维菌素对于盘尾丝虫蚴的杀伤力之
强令人匪夷所思:以每公斤体重150微克的剂量,一年口服一次
就足以杀灭所有的盘尾丝虫蚴!
通过了严格的安评之后,默沙东制药决定将兽用伊维菌素用
于河盲症的治疗。但是,由于河盲症仅发生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
非洲国家和少数拉美国家,美国没有病例,所以河盲症不是FDA
的注册疾病,将伊维菌素用于河盲症根本就无法在美国申请报
批。
[15]
好在旅居法国的非洲移民中有少数河盲症的病例,使它
成为法国医药管理部门的注册疾病,于是默沙东将人用伊维菌素
(商品名改为Mectizan)在法国申报,并获得批准。
慷慨解囊:史无前例的医药捐赠
新的问题又来了:如何才能将伊维菌素送到当地居民的手
里?那些国家没有健全的医保和公共卫生系统,很多地方连公路都没有,有些偏僻的村寨甚至连越野车也开不进去。
尽管每年只需口服一次,但谁来为这些伊维菌素的生产和销
售买单?不管药价定得多低,那近2000万河盲症患者和8000万受
河盲症威胁的非洲老百姓都不可能买得起。而免费捐赠又有悖于
必须依靠利润才能有巨额资金投入新药研发的现代制药工业模
式。面对这个两难的选择,从主管研发的副总裁晋升为默沙东首
席执行官的瓦杰洛斯博士说服了董事会,毅然决定向全球所有被
盘尾丝虫感染和受到感染威胁的人群无限期无偿提供伊维菌素,直至河盲症这一公共健康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默沙东的这一决定,他们认为上市的制
药公司应该为它的持股人提供最高的红利,而不应该牺牲持股人
的利益来参与慈善事业,因为那是慈善机构该做的事。然而,这
一举动充分体现了默沙东一以贯之的“以人为本”和“为社会提供更
好的产品和服务”的宗旨,赢得了社会的尊重,极大地提高了默
沙东研究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献身精神,也使默沙东成为有志于医
药工业的年轻人心目中理想公司的首选,被美国《财富》杂志连
续7年评为“全球最令人敬佩的公司”。
现代制药是一项尖端科技产业,涉及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
优秀科技人才的聚集大大提高了默沙东的科研水平,确立了默沙
东在制药界的领先地位。长期以来,默沙东实验室在基础医药
学、化学、生物技术等各个生命科学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
性的进展,一直被学术界的广大同仁所推崇,享有很高的声誉。
每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研究人员都要发表相当数量的高水平
学术论文,足以跟世界一流大学和研究所比肩,他们经常被邀请
去大学、研究所和各种学术会议做演讲。反过来,默沙东实验室
每年也邀请许多大学和研究所的著名学科带头人,以及学术界年
轻的后起之秀来做演讲,进行学术交流。许多原本看好学术机构
的科研人才纷纷加入默沙东实验室,年轻的博士毕业生和博士后
更是以加入默沙东实验室为荣,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业界的同行不无妒忌地戏称默沙东实验室拥有世界一流大学生命学科
博士毕业生的首轮“选秀权”。
以人为本的精神吸引了优秀的人才,优秀的人才创造出了更
优秀的科技。从长远看,默沙东的捐赠决定还是为它的持股人带
来了更多的利益。
功不可没:指日可待的河盲绝灭
制药是为了救死扶伤,祛病消灾,在这个层面上,伊维菌素
对提高和改善整个人类的健康状况和生活条件的贡献是无法用金
钱来衡量的。从1988年开始,默沙东与卡特基金会合作,在众多
志愿者的参与下,持续向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各个非洲国家分
发伊维菌素。随后,伊维菌素的无偿捐赠又扩展到拉丁美洲的安
提瓜、危地马拉、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等国。鉴于在
非洲国家和也门丝虫病和河盲症并存,1998年默沙东将伊维菌素
捐赠项目扩展至丝虫病的治疗。
截至2012年,默沙东已为非洲、拉丁美洲及也门的11.7万个
群体捐赠了价值51亿美元的伊维菌素片,并为伊维菌素捐赠项目
提供了约4500万美元的直接资金支持。在拉丁美洲的6个流行国
家中有4个国家的河盲症传播已被遏制,在5个非洲国家的9个地
区的传播也同样被遏制,没有新病例出现。
默沙东公司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福维泽说:“25年后,伊
维菌素捐赠项目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在全世界逐步实现消除河
盲症这一长期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带来改变,这是振奋人心
的。我们惊叹于这一合作联盟在保护后代免受河盲症病痛中的突
出表现,河盲症会给患病者及其家人、医疗系统和当地经济带来
灾难性的后果。捐赠项目的成功表明:通过合作,我们可以成功
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健康问题,即使是容易被忽略的地区和容易
被忽略的疾病。”独特的公私团体合作使伊维菌素捐赠项目的实施成为可能。
这一合作的参与者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全球卫生工作
组、非洲盘尾丝虫病控制项目(APOC)、美洲盘尾丝虫病根除
项目(OEPA),以及流行国家的卫生部门、非政府发展组织和
当地团体。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也表示:“默沙东的伊维菌素捐赠项目
史无前例,25年来在为河盲症患者减轻病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
展。之前我们对解决非洲河盲症的预期仅是控制,但目前一些非
洲国家在彻底消灭河盲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西半球,卡特
中心及其合作伙伴几乎将河盲症彻底根除。因为默沙东的贡献、病症流行国家的支持以及强大的合作,我们可以预见一个没有河
盲症的世界。”
每年的10月11日是世界视力日,启动伊维菌素捐赠项目30年
后的今天,默沙东与合作伙伴共同庆祝了在消灭河盲症进程中取
得的重大进展。河盲症是世界范围内导致可预防性失明的主要原
因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伊维菌素的无偿捐赠有希望使河
盲症在2020年前后从地球上绝迹,可以说是继牛痘灭绝天花之
后,人类医药健康史上又一个伟大的成就。喜欢本书吗?更多免
费书下载请***:YabookA,或搜索“雅书”。
2011年5月初稿于新泽西
2017年8月修改稿于新泽西第四章 遭遇“黑天鹅”的有准备之人
保列治和保发止的发现
原始制药(确切地说应该是找药)都是没有分子靶标的。从
神农尝百草开始,一直到生命科学发展到分子水平之前,找药都
是直接针对疾病症状的。这样做,成功的几率很低,因为只能做
表观的筛选而无法进行系统性的优化,基本就是碰运气。更重要
的是,在没有动物疾病模型的情况下,直接在自己或患者身上试
药是非常危险的,传说中的神农氏就是因为误食“断肠草”而客死
他乡的。
不期而终的荷尔蒙研究
现代分子生物医学的创立,使我们在近几十年里对许多疾病
的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比如人体胆固醇的调控,包括胆固醇的
生物合成和转移,摄入胆固醇的吸收和代谢,以及胆固醇与心脏
病之间的联系,等等。基于这些基础研究的结果,以羟甲基戊二
酰辅酶A还原酶(HMG-CoA reductase)为药靶,默沙东等几大制
药公司先后研发出了历史上销售量最大的“他汀”(Statin)类药
物,如舒降之,大大降低了冠心病患者心梗的风险。
[16]
可是,在很多情况下,在早期研究中被看好的分子药靶要么不能被验
证,要么与毒性相关,甚至可能因为没有合适的市场,而得不到
进一步研发。
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默沙东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就开始了
对男性荷尔蒙的研究,希望能找到治疗青春期粉刺的新药。青春
期是性荷尔蒙活动的旺盛期,随之出现的青春期粉刺多半与男性
荷尔蒙的活动有关系。当时主要有两个已知的甾体类雄性激素(Steroid hormones):睾丸酮(Testosterone)和作用更强的二氢
睾丸酮(Dihydrotestosterone, DHT),默沙东的研究团队认
为,如果抑制将睾丸酮转化为二氢睾丸酮的5-α还原酶,应该可以
降低体内男性荷尔蒙的活动,也许可以抑制粉刺的生长。
基于这样一个假设,默沙东实验室组成了多学科的项目团
队,一方面深入研究青春期粉刺与男性荷尔蒙活动的关系,试图
从机理上验证该项目的可行性,另一方面积极寻找高活性、高选
择性的5-α还原酶的抑制剂。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合成了相当数
目的新型抑制剂,同时也建立了一整套生物测试方法,用于筛选
和评估这些新型的抑制剂。更重要的是,他们还积累了大量的有
关二氢睾丸酮和5-α还原酶的数据和知识。制药项目的进展,说到
底就是有关该疾病与分子靶标的知识积累。随着知识的不断积
累,项目团队才有可能设计出理想的化合物。
但是,随着项目的进展,公司意识到,给青少年使用甾体类
激素药物是难以被社会接受的,即使研发成功,市场营销的困难
也将会很大,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终止了5-α还原酶抑制剂的
研究项目。
多米尼加的古怪病例
几乎就在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加勒比海岛国多米尼加发生
了一件听上去毫不相干的事情。一个来自偏远部落的小女孩因病
被送进医院做腹腔手术,结果医生发现“她”实际是个男孩!谁也
没想到,若干年之后,这个意外发现给5-α还原酶抑制剂的研究项
目带来了转机,并最终促成了不止一种,而是两种新药的发现。
康奈尔大学医学院和西南医学中心的科学家们首先注意到了
这个不寻常的病例,他们深入丛林,对那个偏远部落的人群进行
了几年的跟踪研究,发现该地区的许多男性都有类似的经历。他
们出生时外生殖器呈雌性,所以被当成女孩来抚养。但到了发育
期间,他们的雄性特征开始显现,并长出男性外生殖器,成为男人。1974年,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教授朱丽安·英珀拉托-麦金利在
一个讨论新生儿生理缺陷的学术会议上首次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
果。
他们发现,这些所谓的“假双性儿
童”(Pseudohermaphrodites)其实都是男孩,只是在出生时,他
们的性腺(Gonads)尚未长成,所以外生殖器呈雌性,被误认为
是女孩。青春期时,他们的性腺开始发育,大多能长出男性生殖
器,成为正常男人。这些在发育期“变性”的男人进入老年以后不
会脱发变成秃头(男性型脱发[Male pattern baldness,简称
MPB]),他们的前列腺相对都很小,而且老年时也不会增生。
这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丛林深处的部落,与外界的接触很有
限,所以他们的遗传基因也与外界相对隔绝。假双性儿童的现
象,很有可能是某种遗传共性的表象。果不其然,进一步的遗传
学研究结果显示,这些特殊的多米尼加部落男性体内二氢睾丸酮
的含量大大低于正常男性的水平,因为这些部落的大多数男性有
一个共同的遗传缺陷:他们都缺少将睾丸酮转化为二氢睾丸酮的
5-α还原酶。
掠过天际的黑天鹅
药物研发与所有科学研究一样,是在探索未知的世界。
但是“未知”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已知的未知”(Known
unknown),另一类是“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这
话听起来有点绕,下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就明白了。
某地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煤炭,于是有人就组织了一支勘探
队到附近别的山洞里也去找煤炭。是不是能找到煤炭?没有人知
道,这就是已知的未知。但是他们找来找去,没有找到煤炭,却
在另一个山洞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古代的墓葬,有大量的陪葬
品。山洞里的古代墓葬在被发现之前就是未知的未知,所以不会有人专门去找。现在有人发现了,那就会有更多的探险队去寻
宝,这时的古代墓葬就不再是未知的未知了。在这个例子里,如
果把煤炭和古代墓葬换过来,先发现的是古代墓葬,在寻找更多
古代墓葬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煤炭,那么古代墓葬就是已知的未
知,而煤炭则成了未知的未知,就看你的初始条件是什么。
已知的未知有很多,严格来讲,每一个科学家的工作都是在
试图发现某一个或几个已知的未知。所有立项的新药研发也是一
样,都是在寻找已知的未知,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要找什么,有
靶点,有目标,不管最后找到找不到,都属于已知的未知,这里
包括研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多种事件,比如心律紊乱、肝脏代谢
酶受阻、肾功能受损等,尽管这些结果都无法预见。因为我们事
先知道这些情况有存在的可能性,并且一定会刻意去筛查,如果
它们一旦发生了,项目团队也都有应对的策略,所以它们都属于
已知的未知,只是出现的几率有大有小而已。
那么未知的未知有多少呢?回答是“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就
不再是未知的未知,而是已知的未知了。著名作家纳西姆·塔力布
在他的畅销书《黑天鹅》里把这种未知的未知比作“黑天鹅”,使
它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术语。
在18世纪欧洲人发现澳洲大陆之前,他们见过的所有天鹅都
是白色的,所以在当时欧洲人的眼中,天鹅就只能是白色的。直
到欧洲人发现澳洲,在第一次看到当地的黑天鹅之后才认识
到,“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个一般性结论是错误的。仅仅一只
黑天鹅的出现,就颠覆了前人从无数次对白天鹅的观察中所归纳
出的一般性结论,引起了人们对认知的反思——以往认为对的不
等于以后总是对的。
这些黑天鹅是不可预见的,它们一旦掠过天际,便会影响巨
大。
慧眼识珠的有准备之人在不断探索未知的科学领域里,遭遇黑天鹅其实并不是太
难,难的是认识黑天鹅。
牛顿是第一个被树上掉下来的果实砸到脑袋的人吗?从概率
上讲几乎不可能是,但在牛顿之前,没有人认识到这是一只“黑
天鹅”,它揭示了一个很重要、但在当时不为人知的存在。正在
研究运动学的牛顿提出了“苹果为什么不往天上升,而是往地上
掉”这一关键问题,认为有一种未知的“力”在起作用,于是我们有
了划时代的万有引力定律。弗莱明爵士是第一个注意到青霉菌落
的周围有个亮环的人吗?从记载来看也不一定是,但在弗莱明之
前,没有人认识到这也是一只“黑天鹅”,它也揭示了一个很重
要、但在当时不为人知的存在。正在研究细菌学的弗莱明意识到
了这些亮环应该是无菌的区域——“这些青霉菌落里一定有些什
么奇妙的东西”,并且花了大量时间去寻找到这个“奇妙的东西”,于是我们有了突破性的抗菌新药——青霉素。
1948年,美国佐治亚医学院药理学家雷蒙德·P.安奎斯特
(Raymond P. Ahlquist)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没想到成文
投稿之后却被一家著名的科学杂志拒绝了,他不得不通过熟
人“走后门”才在《美国生理学》杂志上发表。他在该文中指出:
如果有两种不同的肾上腺素受体(α-受体和β-受体)存在,那么
肾上腺素与去肾上腺素之间相互矛盾的生物效应就很容易解释
了,因为它们调控不同的生物回路。安奎斯特的这个观点在当时
实在是太颠覆了,就好像是在说“天边飞过的那只黑鸟也许是一
只天鹅”。那些看惯了“白天鹅”的同行们当然都认为他看花了眼,所以发表之后也没人关注,以至于整整十年之后才有识货的学者
站出来说:我认为那真的就是一只黑天鹅,值得我们去找一找。
他就是英国著名药理学家詹姆斯·W.布莱克(James W. Black)爵
士。
为了找到这只黑天鹅,布莱克辞去教授职位,加入英国ICI制
药公司,并成功地说服了公司领导,率队立项研发选择性的肾上
腺素β-受体拮抗剂,这在当时还不存在。这时的“黑天鹅”其实已经不黑了,因为有了安奎斯特的大胆假设,它经历了从未知的未
知到已知的未知的关键性转变。十年求索,几度沉浮,布莱克领
导的研发团队终于找到了那只最先被安奎斯特根据一鳞半爪的实
验数据推测出来的“黑天鹅”,成功地研发出了一类创新药物β-受
体阻断剂(β-Blocker)。这一巨大成功不但使蛋白质受体亚型成
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事实,而且布莱克本人也修成正果,荣获
198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安奎斯特呢?好在还是有人想到
了他。1976年,他与布莱克共享了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17]。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我们头顶的天空上不断飞过的各种东
西里边,时不时就会有无人知晓的、真正的“黑天鹅”。其中有一
些招摇过市,能立刻引起轰动,但还有很多悄然掠过,只给我们
留下短暂的一瞥。
康奈尔大学和西南医学中心对加勒比海岛部落民“假双性
人”的遗传学研究结果是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每个新药研发人
员都看得到,好比一只“黑天鹅”从闹市的上空飞过。但是,在这
个“闹市”(新药研发圈)里看热闹的人群中,有这么两位识货的
行家:一位是当时默沙东的首席科学家瓦杰洛斯博士,另一位是
曾经领导默沙东5-α还原酶抑制剂项目的科学家格伦·亚斯(Glen
Arth)博士。他们俩手里拿着刚打印出来的同一篇文献,冲出办
公室,相遇在楼道里……
良性增生的前列腺
这篇有点旁门左道的遗传学研究报道,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只是科学的花边新闻,但是不久前认真研究过5-α还原酶的默沙东
的科学家们却敏锐地意识到:5-α还原酶的抑制剂也可以降低正常
人体内二氢睾丸酮的含量,也应该可以用来防止和治疗老年性的
良性前列腺增生(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简称BPH)。用
甾体类药物给青少年治疗青春期粉刺也许没有什么市场,但用于
老年人的前列腺增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5-α还原酶抑制剂的目标不应该是青年人的粉刺,而应该是老年人的前列腺。
前列腺是男性特有的性腺器官,具有内、外双重分泌功能的
性分泌腺。作为外分泌腺,前列腺每天分泌约2毫升前列腺液,是构成精液的主要成分;作为内分泌腺,前列腺分泌的激素称
为“前列腺素”。前列腺位于膀胱底部,尿道从它的中间穿过。进
入更年期后的男性,由于性激素代谢的变化,会因为不同程度腺
体和(或)纤维、肌肉组织增生而造成前列腺体积增大。增生的
前列腺挤压尿道,导致一系列排尿障碍症状,如尿频尿急、夜尿
增多、尿流细弱、尿不尽等。这些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许多严重的并发症(如急性尿潴留、结
石、肾积水和肾功能不全等),甚至会危及患者的生命。良性的
增生大多发展缓慢,往往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排尿障碍症状也
被认为是正常的衰老过程。
据统计,全球约有1.05亿人受到影响。
[18]
在50岁以上的男
性人群里,显现出不同程度的良性前列腺增生临床症状的人数约
占50%(每两人中就有一个,还不包括已有增生但尚未出现临床
症状的人群),[19]
而在80岁以上的男性人群里,有临床症状的
前列腺增生患者高达90%。
[20]
毫不夸张地讲,每个男人上了年
纪,他的前列腺多多少少是要增生的。现代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所以受前列腺增生困扰的老人也就越来越多。当时没有有效的药
物能防治前列腺增生,重症患者必须动手术切除增生的部分,疏
通尿路,所以新型有效药物的潜在市场应该是相当大的。
保列治与保发止
将靶标锁定在前列腺之后,默沙东重新启动了5-α还原酶抑制
剂的研究项目。又经历了十几个冬夏之后,默沙东实验室的科研
团队终于将保列治(Proscar,药名为非那雄胺[Finasteride])申报FDA批准,并于1992年投放市场,成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
的第一个口服药物。在临床试验过程中,保列治显示的功效比预
计的要好很多,它不但阻止了前列腺的增生,而且还能使已经肥
大的前列腺缩小20%~25%,大大减少了手术治疗的必要性。
泌尿科的医生一开始不以为然,甚至不太情愿开处方让病人
服用保列治,他们的理由是手术治疗见效快,而服用保列治则需
要时日;另一方面,他们不想看到手术病人的快速减少。为了打
开保列治的市场,默沙东决定直接向最终的消费者——患者——
做广告,让他们了解手术治疗以外的选择和药物治疗的优缺点,成为最终的受益者。处方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大规模广告宣传在
美国制药界是首创,颇有争议。舆论认为,制药公司的钱应该花
在新药研发上,而不应该花在市场营销上。但事实证明,让消费
者了解新药的功效也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保列治的上市没有引起
爆发性的轰动,但还是逐渐被患者和医务人员所接受。口服保列
治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其处方销售也稳步上升。
保列治治疗前列腺增生的成功使默沙东的科研人员有机会进
一步研究5-α还原酶与男性型脱发之间的联系。男性型脱发是因为
头皮中的双氢睾酮含量增加,使得毛囊逐渐萎缩,头发变细,头
发数量减少。经过几年资源的大量投入之后,第二个5-α还原酶抑
制剂药物保发止(Propecia)在1997年上市了。保发止和保列治
的有效成分是相同的,只是剂型和剂量不同。在为期5年的临床
试验里,已开始部分脱发的男性服用保发止后都没有进一步脱
发,其中约66%的患者还长出了一些新的头发,而服用安慰剂的
患者却继续脱发。独立的照片分析结果也表明,服用保发止的患
者中有48%头发明显增加了,另外42%则没有继续脱发,效果是
显著的。
中国目前大约有1.3亿的男性型脱发患者,但是去医院接受正
规治疗的还不足三成。很多患者在脱发初期用生姜擦头皮、防脱
洗发水等错误方法,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通过服用保发止可降
低体内双氢睾酮浓度,服药后3个月脱发开始减缓,6~9个月新头发开始生长,1~2年可达最好疗效。当然,任何药物都有副作
用。5-α还原酶抑制剂的主要副作用是少数服药者会出现性功能减
弱,个别病人甚至会出现阳痿。对于前列腺增生的老人,这个风
险也许已经不再重要,但对于脱发的青壮年,却需要认真权衡其
中的利弊。
医学界对那些多米尼加部落人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那里的
男性除了不脱发和没有前列腺增生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前
列腺癌症的患者。为此,默沙东实验室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合
作,开展了大规模的长期临床试验,研究保列治对前列腺癌的防
治作用,目前尚无定论。
机遇垂青于有准备之人
保列治和保发止的发现又一次印证了著名科学家路易·巴斯德
的名言:“机遇垂青于有准备之人。”20世纪60年代默沙东实验室
对男性荷尔蒙和5-α还原酶的研究,为日后保列治的研发打下了很
好的基础,不但积累了合成这类化合物的经验,建立了有效的酶
活性生物测试方法,更重要的是,积累了有关睾丸酮、二氢睾丸
酮和5-α还原酶的知识,为寻找这个代谢途径里的相关药靶做好了
准备,并且密切关注这一领域里的科研新动向。所以,到了20世
纪70年代中后期,有关多米尼加“变性人”的报道及其跟踪研究立
刻引起了默沙东科研人员的注意,他们抓住了这个貌似毫不相
关、很容易被忽略的机会。
中国目前的基础生物医学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人力和物力
的总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而通过独立自主的基
础研究来发现和验证新的药靶投入高,周期长,很难在短时期内
成为主流方向。但是,中国的医药界精英应该注意积累各种常见
病、多发病的病理知识,密切关注全球基础生物医学研究的新动
向和新发现,做有准备之人。
没人能准确预测下一只“黑天鹅”会在何时何地出现,但发现和捕捉到下一只“黑天鹅”的人一定是有准备之人。喜欢本书吗?
更多免费书下载请***:YabookA,或搜索“雅书”。
你准备好了吗?
2013年1月初稿于新泽西
2017年10月修改稿于新泽西第五章 从后继专利药到更优专利药
降压药依那普利的成功逆袭
新药研发的竞争是白热化的,原因之一是,已知可用药的生
物靶标(Drugable targets)是有限的,一经临床前的药理验证
(Pharmacological validation),或是更进一步的临床验证
(Clinical validation),各大公司的研发资源就都集中在了这些
有限的药靶上了。成功希望越大、市场前景越看好的药靶,竞争
就会越激烈。就拿二肽酰肽酶-4抑制剂的研发来看,默沙东原创
的西格列汀(Sitagliptin)
[21]
成功之时,已有十多家药厂的格列
汀类的候选药物先后进入了临床试验,力争在后继专利药中取得
领先地位。更为理想的当然是能在疗效、安全性或是依从性等方
面超过已经上市的专利药,后来居上成为更优专利药。
对跨国大药厂来说,创新药是首选,更优药其次,后继药则
是不得已的选择。创新药物一般可占据市场份额的60%~80%;
更优药如果在疗效、安全性或依从性方面确有优势,一般能够后
来居上,占据市场的主要份额(>50%)。但是疗效和安全性大
致相仿的后继药,基本上只能有10%~20%的市场份额,所以在
大量的资源投入之后,如果不能争其先,就必须求其上。20世纪
70年代中后期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简称ACE)抑制剂的研发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实例。
关于血压的是非曲折
在1628年出版的《心脏与血液的运动》一书中,英国医生威
廉·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总结了前人和他自己的研
究工作,提出了相对完整的血液循环理论,从此人类对于“心血管系统”的理解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过了一百多年,英国牧师斯
蒂芬·海尔斯(Stephen Hales)于1733年首次公布了血压的测量方
法,但是血压测量在临床医学上的真正普及,则一直要到1896年
基于袖带的血压计发明之后,从此操作变得十分简便。
进入20世纪,随着血压测量数据的累积,将血压升高作为疾
病的描述也日益增多。在高血压患者中,绝大多数是原发性的,约占95%,发病的原因还不清楚,但往往与家族病史相关,可能
是环境和遗传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1928年,美国梅奥诊所的医
生描述了一种特殊的高血压,伴有严重的视网膜病症,但肾功能
正常。因为患者通常在一年内因中风、心力衰竭或肾功能衰竭而
导致死亡,所以它被称为“恶性高血压”(Malignant
hypertension)。
虽然严重或恶性高血压对健康的威胁很早就得到了充分的认
识,但所谓的“良性”血压升高的风险及其治疗一直是有争议的。
早在1931年,利物浦大学医学教授约翰·海(John Hay)就认为,高血压患者面临的最大风险就在于我们发现了它,因为肯定会有
一些傻子去设法降低它。美国著名的心脏病学家保罗·D.怀特
(Paul D. White)在1937年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虽然
我们确信自己能够控制,但高血压也许是一个重要的补偿机制,不应该被随意扰动。”查尔斯·弗里德伯格(Charles Friedberg)在
1949年的经典教科书《心脏疾病》中指出,“患有‘轻度良性’高血
压的人不需要治疗”,而当时对“轻度良性”高血压的定义是血压为
210100 mmHg。
从20世纪50年代起,心肺医学主流意见的大潮发生了转向,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良性”的原发性高血压并不是无害
的。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析报告和跟踪研
究(例如1974年美国国立卫生院心肺研究所发表的《弗雷明汉心
脏研究》
[22]),积累的证据表明,“良性”高血压也会导致心血
管疾病和增加死亡的风险,在普遍的高血压患者群中,这些风险
随着血压的升高而逐渐增加。与此同时,基础医学对于血压调控的机理研究也逐渐深入到
了分子水平,使得小分子化学介入成为可能。
血压调控与化学介入
血管紧张肽原酶(Renin)是人类最早发现的蛋白酶,距今
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一百多年里,由血管紧张肽原酶和
血管紧张肽所构成的生物调控体系(Renin-angiotensin system,简
称RAS或RAAS
[23])一直是基础医学和临床研究的热门领域,因为RAAS对人体的体液和电解质平衡以及血压的调控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简单地讲,当人体内血量降低(失血)时,肾脏就会
释放血管紧张肽原酶。血管紧张肽原酶将储存于肝脏内的血管紧
张肽原(Angiotensinogen)通过降解转变为血管紧张肽-
Ⅰ(Angiotensin-I),新产生的血管紧张肽-I在肺循环
(Pulmonary circulation)过程中被血管紧张肽转换酶(ACE)进
一步转换为血管紧张肽-Ⅱ。血管紧张肽-Ⅱ作为激动剂
(Agonist)将其受体(Angiotensin-Ⅱ receptor)激活,从而引起
下游一系列相应的生理变化,最终导致血管壁紧缩,血压升高。
这是人体自我保护、保障器官供血的重要机制。
与此相反,血管舒缓激肽(Bradykinin)则通过另一类受体
(Bradykinin receptor)而引起血管舒张,降低血压,达到平衡,以避免因血压升高而可能导致的一系列不良反应。对于高血压患
者来说,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吸烟、酗酒、肥胖、精神压力等,他们的RAAS调控体系的平衡点发生了偏移,血压被维持在较高
的状态下,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增加了心梗、脑梗等突发性病变
的风险。
长期以来,各大药厂的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寻找能干预
RAAS调控体系的小分子,通过阻断或促进其中的某个环节而降
低血压,建立新的调控平衡。值得注意的是,血管舒缓激肽与血
管紧张肽一样,主要也是在肺循环的过程中被血管紧张肽转换酶ACE降解的,由此不难得出结论,血管紧张肽转换酶对血压调控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血管紧张肽转换酶抑制剂(ACE
inhibitor)就是20世纪80年代从RAAS体系中研发出来的第一类高
效降压药——普利类降压药。
[24]
1981年4月,施贵宝制药在各大药厂的ACE抑制剂项目的竞
争中脱颖而出,将第一个普利类降压药卡托普利(Captopril,商
用名Capoten)推上了市场,开启了RAAS体系药物研发的新时
代。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又有十多个普利类的降压药陆续上市,可见医药界对ACE抑制剂研发的投入之多,竞争之激烈。
卡托普利与药物设计
卡托普利的成功给药物化学带来了实质性的进步,以化学结
构为基础的新药设计(Structure-based drug design)从此进入主
流,成为应用最普遍的药物化学方法之一。
20世纪70年代初,巴西科学家从美洲洞蛇(Bothrops
jararaca)的毒液中发现了一组多肽,能够增强血管舒缓激肽的功
效,被命名为“血管舒缓激肽增强因子”(Bradykinin potentiating
factor,简称BPF)。剑桥大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BPF能抑制从血
管紧张肽-Ⅰ到血管紧张肽-Ⅱ的转化,正是血管紧张肽转换酶的
抑制剂。这一重要的发现,给原来无从下手的药物化学家们提供
了一个出发点。但是如何把这些因为药代动力学性质不佳而不能
开发成口服药物的多肽分子转化为可开发的化学小分子,在当时
是一个十分前沿的课题。
施贵宝制药研究团队以这些天然的多肽类ACE抑制剂为起
点,采用当时很先进的定位突变(Site-directed mutagenesis)生物
技术
[25]
,仔细研究了BPF的构效关系(Structure-activity
relationship,简称SAR)。他们发现这些多肽C末端的脯氨酸残基
对ACE的抑制活性非常重要,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药效基团”(Pharmacophore)
[26]。以这个脯氨酸残基为核心,施贵宝
制药团队合成了2000多个衍生物,通过生物测试,他们发现在脯
氨酸附近引入巯基(Thiol group,或-SH)能进一步提高化合物对
ACE的抑制活性。在巯基和脯氨酸残基这两个结构单元的基础
上,他们找到了高效率的ACE抑制剂,成功地设计出了卡托普利
(见图5-1)。
图5-1 卡托普利
在整个研发过程中,施贵宝的团队把化合物结构单元放在首
位,通过对药效基团的定位(Pharmacophore mapping)建立构效
关系,逐步向高效率的ACE抑制剂靠拢,直至最后成功地设计出
卡托普利。这是第一个以化学结构为基础的新药设计的成功例
子,从那以后,这种先进的思想方法得到了广大药物化学家的接
受,成为现代药物化学的主流。
伊纳普利与更优药物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关键性的巯基给卡托普利带来的对血管紧张肽转化酶的高效抑制,使施贵宝占得了开发普利类药物
的先机;但是,巯基也给卡托普利带来了与其相关的副作用,给
其他药厂后继药的研发留下了提高的空间。
面对施贵宝在ACE抑制剂研发方面的领先局面,默沙东实验
室的研究人员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卡托普利的研发,尤其是其临床
试验的结果。含巯基的卡托普利化学结构一经发表,默沙东实验
室的课题组立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基于从其他项目得来的
类似经验,大家认为巯基很有可能造成三种类型的副作用:白细
胞降低、皮疹和影响味觉。于是,默沙东的课题组把设计不含巯
基的ACE抑制剂作为新的目标,力争研发出同样高效,但更安
全、副作用更小的普利类新药,成为更优专利药。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施贵宝的ACE抑制剂的构效关系已经
显示,巯基是卡托普利与ACE结合的主要官能团,置换巯基会大
大减少该化合物与ACE的结合能,丧失抑制功效。反应过渡态机
理研究结果表明,ACE是一种金属蛋白酶(Metalloprotease),锌离子参与了它所催化的降解反应,而巯基则是已知的很强的锌
离子键合基团,正是这两者的结合有效地抑制了ACE的催化活
性。那么,有没有不含硫的锌离子键合基团呢?答案是肯定的。
可是将这些已知的锌离子键合基团引进分子之后,对ACE的抑制
活性不够强,效果不理想。
就在默沙东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积极寻找其他锌离子键合基团
时,卡托普利的临床研究报告公布了。卡托普利的降压效果很
好,但在高剂量时果然出现了一些副作用。部分高血压患者服用
卡托普利后会出现白细胞降低和皮疹,还有一部分患者的味觉受
到影响,严重时甚至会暂时失去味觉。这些副作用决定了卡托普
利只能服用较低的剂量。另外,卡托普利的药代动力学参数也不
够理想,尤其是半衰期较短,患者每日必须服药2~3次,给长期
服用造成相当大的不便。这些预料之中的结果增强了默沙东管理
层和研究团队的信心,他们投入了更多的资源,终于在一年多的
时间里,找到了一种新型的组合。在先导化合物的优化过程中,默沙东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发
现,虽然用羧基直接取代巯基的效果不佳,但羧基和苯乙基的组
合效果却很好,这就是后来的“依那普利拉”(Enalaprilat,见图5-
2)。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依那普利拉对ACE的抑制活性(Ki为
0.2 nmolL)虽好,但口服生物利用度(Oral bioavailability,或
F%)很低,半衰期仅为1.3小时。为了赶超卡托普利,默沙东的
团队应用了“前体药”(Pro-drug)
[27]
的概念,将依那普利拉的羧
基转化为乙酯,成功地研发出了第二个在美国被批准使用的ACE
抑制剂——依那普利(Enalapril,商用名Vasotec,见图5-2)。
图5-2 依那普利拉(R=H),依那普利(R=Et)
依那普利本身的活性并不高,必须经肝脏的酯酶水解后才能
产生高活性的二羧酸依那普利,即依那普利拉。依那普利口服后
吸收迅速,生物利用度约60%(不受食物影响),虽然依那普利
在1小时内达到血浆峰值浓度,但依那普利拉则需3~4小时才能
达到血浆峰值浓度。依那普利拉与ACE的结合非常紧密,因此血
浆半衰期约为11小时,非常适合每日一次的服药间隔。除了普利
类药物共有的一些轻微的副作用(如干咳)外,依那普利即使在
高剂量服用时也没有发现白细胞降低、皮疹和丧失味觉这些卡托
普利特有的副作用,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由于上述优点,依那普利在1985年12月被批准上市以后,销
售额迅速而又稳步地上升。尽管比卡托普利晚了4年半,但它很
快就在全球范围内超越卡托普利,成为ACE抑制剂降压药的首
选。到了1988年,依那普利已经成为默沙东制药史上第一个年销
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大药。
从依那普利的成功逆袭可以看出,要在竞争白热化的新药研
发领域取得成功,除了要有敏锐前瞻的眼光,能够从基础医学研
究的最新进展中发现可以用药的靶标外,还必须知己知彼,善于
从竞争者已知的临床试验新药,或者已经批准上市的专利药里找
到提高和优化的空间,争取后来居上。
依那普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它不是完美的,高血压的治
疗并没有就此止步不前。前面提到,维持一定的血压是至关重要
的,所以在RAAS调控体系中,有许多反馈的回路和补偿机制。
仅靠抑制ACE的活性,仍然不能有效地治疗不同类型的严重高血
压患者。2000年,全球范围内仍有将近10亿人患有高血压,其中
发达国家约占3.3亿,发展中国家约占6.4亿。在成年人中,高血
压患者的比例更是高达26%(每4人中就有1个患者),其中男性
的比例略高于女性。
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的成年
人中高血压患者大约有7500万,占32%。2014年,美国以高血压
为主要原因的死亡人数超过41万,每天就有大约1000人死亡。
2004年10月发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现状》
[28]
调查结果显
示,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高血压患病率为18.8%,估计全国患病
人数超过1.6亿。虽然患病率略低于发达国家,但上升趋势明显,与1991年相比,患病率上升了31%,患病人数增加约7000多万
人。到了2011年,《北京健康白皮书》显示,北京市18~79岁的
常住居民中,高血压患病率为33.8%,其中18~30岁男性为18.4%
(每5人中有1人),30~40岁男性为31.1%(每3人中有1人),40至50岁男性已接近50%(每2人中就有1人),40~50岁的女性
患者亦高达30%。因此提高对高血压病的认识,对早期预防和及时治疗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一项大规模的荟萃分析中,血压升高与心血管事件风险之
间清楚地显示了持续的、一致的和独立的相关性。
[29]
该分析包
括了100万名40~89岁、无心血管病史的高血压患者,平均数据
跨度达12.7年(共1270万人年),其中大约有5.6万例死于心血管
性疾病(1.2万例中风、3.4万例缺血性心脏病和1万例其他心血管
病),其他死亡人数为6.6万人。根据此项分析结果,美国高血压
预防、检测、评估和治疗联合委员会在2003年重新定义了高血压
的临床诊断标准。2017年,美国心脏协会再一次降低了(门诊测
量)高血压的指标。根据最近公布的指南,正常血压的标准不
变,收缩压小于120 mmHg,舒张压小于80 mmHg。成人警戒区
被称为“血压升高”,最高收缩压被削减至120~129mmHg,而收
缩压在130~139mmHg之间,或舒张压在80~90mmHg之间为“1
级高血压”,达到或超过14090mmHg为2级高血压。
只要还有高血压患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降压药的研发就不
会停止。在继续深入研究RAAS血压调控体系的过程中,默沙东
又相继把新一代的降压药科素亚(Cozaar)与海捷亚(Hyzaar)
推上了市场。
似曾相识的新药设计
血管紧张肽转换酶抑制剂的成功,说明了血管紧张肽-Ⅱ确实
是引起血压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它可以激活其受体,从而引起
一系列相应的生理反应,最终导致血压升高。因此人们很自然地
想到了直接用血管紧张肽-Ⅱ受体的拮抗剂(A-Ⅱreceptor
antagonist)来抑制该受体的活性,应该可以起到降低血压的作
用。在RAAS血压调控体系中,血管紧张肽-Ⅱ受体是依那普利下
游的靶标,降压的机制更直接,效果也应该更显著。
虽然选择性的血管紧张肽-Ⅱ受体拮抗剂的研发在20世纪70年
代末被普遍看好,但是具体立项却有相当大的困难。当时的情况非常类似于在开发卡托普利时发现“血管舒缓激肽增强因子”的阶
段,只有一个被称为“肌丙抗增压素”(Saralasin)的多肽对血管
紧张肽-Ⅱ受体有一定的拮抗作用,没有适合的小分子作为药物化
学的先导化合物。直到1982年,日本武田制药发表了两项专利,揭示了两种非肽类小分子血管紧张肽-Ⅱ受体拮抗剂,但是活性很
弱。
杜邦制药的科研人员对血管紧张肽-Ⅱ进行了仔细的构象分
析,他们通过二维核磁共振构建了分子的三维构象,再把武田制
药的小分子结构与这个三维构象做重叠比较,找到了武田结构的
欠缺,然后对它们进行改造,使它们更接近血管紧张肽-Ⅱ的空间
构象。这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在看似理性的方法论中有相当比
例的经验工作、化学修饰和生物测试,工作量超过50人年。
最终,他们找到了第一个有口服活性的血管紧张肽-Ⅱ受体拮
抗剂——氯沙坦(Losartan)。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拮抗剂仅在
一种类型的检测中表现出活性,而在另一种类型中则没有。相
反,其他公司报道的拮抗剂却显示出了相反的活性,拮抗第二种
类型的检测,而不是第一种。相比之下,肌丙抗增压素在两种分
析中都有一定的活性。因此,几个不同的科研小组得出了相同的
结论:很可能存在两种不同的血管紧张肽-Ⅱ受体亚型,调节血压
的功能主要来自其中的一个亚型,而且正好就是氯沙坦选择拮抗
的那个亚型!
[30]
默沙东从杜邦制药接手了氯沙坦的开发,经过临床试验后,在1995年把新一代的降压药氯沙坦(商品名科素亚)推上了市
场,而海捷亚则是科素亚与利尿型降压药氢氯噻嗪
(Hydrochlorothiazide)的复方制剂,双管齐下,效果更佳。
研发出疗效更好、更安全的更优专利药,首先获益的应该是
患者,他们的病情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他们的生活质量会进一
步提高,然后才是制药公司。2011年10月初稿于新泽西
2017年11月修改稿于新泽西第六章 当“头号杀手”遇上“头号大药”
从胆固醇假说到他汀4S经典
仔细看一下这三个化学结构式。
图6-1 美伐他汀、洛伐他汀和辛伐他汀化学结构式
看出区别来了吗?
这三个化合物都跟胆固醇(Cholesterol)有关系。化合物1叫
美伐他汀(Mevastatin),是一个天然产物;化合物2叫洛伐他汀
(Lovastatin),也是一个天然产物;化合物3叫辛伐他汀
(Simvastatin),是洛伐他汀的人工衍生物。它们之间的区别就
是一个甲基,这是以碳原子为骨架的有机化合物的最小结构单
元。
[31]
然而,就是这个看似无足轻重、几乎可以被忽略的变
化,给这三个化合物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魏尔啸大胆立说
近年来,胆固醇的名声是越来越坏了。高胆固醇已经成了亚
健康的代名词。超市的货架上摆满了印着“不含胆固醇”字样的各种食品,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高密度”与“低密度”的区别:前者
是“好”胆固醇,而后者是“坏”胆固醇,越少越好。其实,这对胆
固醇来说挺冤枉的。
相传,这个现在家喻户晓的油脂性化学物质最早是由法国化
学家塞尔(Salle)在1769年从胆石(Gallstones)中发现的,但是
到了1815年才有正式的文献记载,被法国化学家谢瑞尔
(Chevreul)命名为“胆固醇”。胆固醇是哺乳类动物细胞膜的基
本结构单元之一,对细胞膜的通透性和流动性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胆固醇也是生物合成各种甾体类激素、胆汁酸(Bile acids)
以及维生素D的前体。人体内胆固醇相对含量最高的器官是大
脑,传递信息的神经细胞膜的结构与功能都与胆固醇密切相关。
毫不夸张地讲,胆固醇是人和动物体内非常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化
学物质。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成年人体内胆固醇的总量在35克左右,分外源性和内源性两种。外源性胆固醇来自食物,每天的摄入量
一般在200毫克~300毫克(素食者低于此量);内源性胆固醇则
是在肝脏中生物合成,每天大约有1000毫克。食物里的胆固醇一
般不容易被吸收,即便有少量被吸收了,它还是会对内源性胆固
醇的生物合成产生抑制作用,从而维持体内胆固醇总量的相对稳
定,所以从食物中摄取的胆固醇对人体内胆固醇的总量以及血液
里的游离胆固醇浓度的影响都不大,这就是调节饮食对降低胆固
醇的作用一般都不大的原因。
胆固醇与冠状动脉硬化和瘀塞之间的联系很早就引起了医学
界的注意,1856年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Virchow)就提出了冠
心病的“胆固醇假说”(Cholesterol hypothesis)
[32]。根据病理解
剖的发现,魏尔啸认为血液里的游离胆固醇在动脉血管壁上的沉
积是造成动脉血管硬化和冠心病的直接原因。这是一个超越时代
的大胆假设,一直到100年后的1956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研究人
员从酵母菌的提取物中分离出了羟甲戊酸(Mevalonic acid),随
后又证实了甲羟戊酸是胆固醇生物合成的中间产物,基础医学对于胆固醇代谢和调控的研究才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其后的几十年
间,人们对胆固醇的生物合成和转移的研究,对摄入胆固醇的吸
收和代谢的认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胆固醇与冠心病之间的联系
也从一个原始的假说逐步上升为医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
远藤章咬定青山
1959年,德国马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在胆固醇生物合
成中起重要作用的物质——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HMG-
CoA reductase)。内源性胆固醇是在肝脏中由乙酸经26步酶催化
的生物反应合成的,其决速步骤就是由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
酶催化的,从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HMG-CoA)到甲羟戊酸根
(Mevalonate)的转化。当外源性胆固醇降低时,羟甲基戊二酰
辅酶A还原酶的表达和活性就会增强,在肝脏内合成更多的内源
性胆固醇,以弥补不足。可见要降低血液里的胆固醇含量,单靠
改变饮食结构、降低摄入量是不够的。于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们开始积极地寻找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的抑制剂。
到哪里去找这种酶的抑制剂呢?日本生物化学家远藤章
(Akira Endo)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在自然界里,有很多微生物
的生长是依赖于胆固醇和类萜化合物的。对于这类微生物来说,胆固醇的生物合成是它们的生命线,而抑制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
还原酶的活性对它们则是致命的。远藤认为,自然界里一定存在
着另一些微生物,它们在生存竞争中以抑制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
还原酶的活性为目标,用“化学武器”去攻击那些依赖胆固醇的微
生物,成为它们的克星,而这种“化学武器”很有可能就是天然的
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
大自然无奇不有,我们应该从哪里下手呢?抱着这个坚定的
信念,凭借他和同行们对于不同微生物的充分了解,远藤领导日
本三共制药公司的团队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辛辛苦苦地筛选了
6000多种不同的微生物。1973年,他们终于从桔青霉菌
(Penicillium citrinum)中找到了第一个天然的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美伐他汀。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是人类
征服其“第一杀手”冠心病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远藤章因此获得
了2006年日本国际奖
[33]
和2008年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
远藤章三共团队的新发现引起了制药界同行的极大兴趣,寻
找天然的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立刻成了新药研发的
大热门。1978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科研团队依样画葫芦,在筛选
了5000多个发酵提取物的样品后,从土曲霉菌(Aspergillus
terreus)中分离出了一个几乎与美伐他汀完全一样的天然产物
——洛伐他汀。两者唯一的区别是,洛伐他汀的3号位上多了一
个甲基。不难想象,与美伐他汀一样,洛伐他汀也是一个高效的
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抑制剂。
经过临床前的药效研究(Efficacy study)和安全评估之后,三共制药率先开始了美伐他汀的临床试验,默沙东的洛伐他汀紧
随其后。但好景不长,1980年,美伐他汀的厄运降临了,一直进
展顺利的临床试验戛然而止了。
默沙东拨云见日
尽管没有正式发表的研究报告,但来自三共制药的内部消息
显示,在为期15周的动物安评试验中,长期服用高剂量美伐他汀
的实验用狗患恶性肿瘤的比例升高。其实任何东西吃多了都可能
会有问题,头疼腰酸等各种轻微的副作用,几乎每个药都有,关
键是看它有多大的安全指数。
[34]
即使是血压升高、肝功能异常
等比较严重的副作用,只要它们是可逆的,即停药后可在短期内
恢复正常,没有后遗症,还是可以在足够的安全指数下谨慎处理
的。但是癌症就不一样了,首先它不可逆,其次它威胁生命。假
设长期服用剂量为每千克体重100毫克时狗患癌症的比例增长了
10%,你愿意冒这个风险吗?三共制药不愿意,药检机构也不可
能批准通过,所以只能停止临床试验。消息传到默沙东,化学结构上只多了一个甲基的洛伐他汀的
开发也无法继续了,因为人们自然而然会推断:两者的化学结构
和生物活性都如此相近,估计毒性也差不到哪里去。为了这件
事,时任默沙东新药研究院主席、资深副总裁的瓦杰洛斯博士几
次亲自前往日本,试图与三共制药联手,共享资源,共同研究美
伐他汀的毒理,但是都被三共制药婉拒了。在默沙东内部,上上
下下对他汀类药物的前景也不乐观。是整个他汀类药物出了问
题,还是只有个别的他汀有问题?
科研需要直觉,但更需要数据。直觉告诉我们,洛伐他汀很
可能有类似于美伐他汀的毒性,但是我们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数
据。停止了临床试验后,默沙东又重新审定了洛伐他汀的安评结
果,在继续进行长期和严格的毒性试验的同时,开始寻找结构上
不同于这两个他汀的新型化合物。
值得庆幸的是,为期两年高剂量的动物毒性试验没有发现洛
伐他汀有任何致癌的迹象,经各方专家的咨询和评审通过,洛伐
他汀的临床试验于1983年底重新启动。数据结果显示,洛伐他汀
对人体也是安全的,它说明了抑制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原酶本
身尽管在高剂量时也有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极少部分患者
会出现肝功能的变化、肌肉的疼痛和痉挛等,但是不会致癌,美
伐他汀的致癌性只是个例,就因为它缺了一个关键性的甲基。
1987年,洛伐他汀经FDA批准成为第一个上市的他汀类药物,获
得了巨大成功。
这个小小的甲基,不但挽救了洛伐他汀,也挽救了整个他汀
类药物,使之成为历史上的“头号大药”——销售金额最大的处方
药物,因为他汀类药物所面对的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冠
心病。
冠心病潜滋暗长
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它的作用就好比是一个永不停息的泵,随着心肌的每次收缩将携带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液经主动脉
输送到全身,以供各器官和组织细胞代谢需要。那么,心脏自身
的氧气和营养又如何得到呢?当然也是从心脏得到的。原来,在
主动脉的根部分出了一条支脉,绕了一个小弯后回到心脏,那就
是负责心脏本身供血的动脉,它的弯形如冠,所以被称为冠状动
脉。
由于脂质代谢不正常,血液中的脂质沉积在原本光滑的动脉
内膜上,形成一些类似粥样物质的白色斑块,造成动脉的硬化和
淤塞,称为动脉粥样硬化病变。这样的病变如果发生在冠状动脉
里,那就成了冠状动脉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
因为冠状动脉的硬化和淤塞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也没有特
征性的临床表现,所以早期诊断很困难,除非做高分辨率的心血
管造影,否则不会被发现。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由于肢体功
能的(正常)下降,大运动量的体力活动逐步减少,对心脏功能
的要求也逐年降低,即使在心脏本身供血不足的情况下仍能维持
正常的生活起居。有不少病例显示,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淤塞
高达90%以上,真可说已经是“命悬一线”,但仍然无明显特异性
症状,偶发的胸闷气短被认为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正因为如
此,冠心病潜在的危险在没有提防的情况下不断地滋长。
由于长期供血不足,冠心病患者的心肌已经变得很脆弱,承
受力大大降低,一些原本习以为常的活动,比如挪动家具、排
便、看紧张的球赛、喝酒、受惊吓等,都会在瞬间超出供血不足
的心脏的负荷。沉积在冠状动脉内壁上的粥样斑块大多数是稳定
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不稳定的“易损斑块”,在心肌活动异常时这
些易损斑块有可能会脱落下来,阻塞血管,引起心肌梗死,在很
多情况下是致命的。
心梗的直接原因是动脉血管的老化和阻塞,而动脉血管老化
和阻塞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就是高胆固醇。舒降之打造经典
在进行洛伐他汀临床试验的同时,默沙东实验室的科学家们
毫不放松,又找到了一个更加安全有效的羟甲基戊二酰辅酶A还
原酶抑制剂,这便是后来的辛伐他汀(化合物3)。辛伐他汀与
洛伐他汀的差别在于:又多了一个甲基。
有了美伐他汀的先例,人们自然会问:在洛伐他汀上加了一
个甲基之后会不会引起一些新的副作用?所以辛伐他汀的药效和
安评必须全部从头来过,不得有一点马虎。实验数据显示,辛伐
他汀是一个功能强大的降胆固醇药物,最高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LDL)50%。其剂量为5~80毫克,对于高密度脂蛋白
(HDL)及甘油三酯的水平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除了他汀类药物
对极少数患者的一些常见的副作用外,辛伐他汀是一个安全且更
有效的降胆固醇新药,于1991年底获得FDA的上市批文,中文商
品名为“舒降之”(Zocor)。
他汀类药物能有效地降低人体血液里的游离胆固醇浓度,但
游离胆固醇只是一个生物标记物(Biomarker)。魏尔啸160年前
的“胆固醇假说”能不能成立?他汀类药物到底能不能减少冠心病
的发病率呢?1994年,默沙东公布了著名的“4S”临床研究结果,为他汀类药物的普遍应用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科学依据。
该临床研究项目的全称为“斯堪的纳维亚辛伐他汀存活率研
究”(Scandinavia simvastatin survival study,简称4S),为期5
年,跟踪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瑞典、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
的冠心病患者共4444人。结果显示,服用辛伐他汀的患者血液里
的游离胆固醇含量平均降低了35%,更重要的是,与对照组相
比,可能的心梗死亡率降低了42%,首次为“胆固醇假说”提供了
最直接的实验数据,成为冠心病临床研究领域里的经典。基
于“4S”临床研究结果,医学界普遍认为,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可以大大降低冠心病患者心梗或者脑梗的风险,延年益寿。中老
年人即使未患冠心病,如果血液里游离胆固醇的浓度偏高,也应该服用他汀类药物,减少或延缓心血管的硬化和阻塞,提高生活
质量。正因为如此,能有效抑制内源性胆固醇合成的他汀类降胆
固醇药物很快成为历史上的“头号大药”,这一类药物的全球年销
售总额高达数百亿美元。
一个小小的甲基,可以把美伐他汀打入冷宫;同样是一个小
小的甲基,也可以使辛伐他汀(舒降之)成为预防和治疗冠心病
的经典。遗憾的是,我们目前还无法预测,哪一个甲基(或是任
何其他基团)会带来毒性或者副作用,哪一个甲基能提高安全系
数或者药效。我们不能轻信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修饰和改动,安
全评估报告可能要泼你一头冷水;我们也不能放弃几乎相同的衍
生物,药效研究的结果也许会给你一个惊喜。
我们必须用数据来说话。
益适纯一波四折
不难想象,由于他汀的巨大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降
胆固醇药物的研究成了各大制药公司的热门。
同在新泽西州,距离默沙东实验室不远的先灵葆雅制药公司
(2009年被默沙东兼并)当然也不例外,他们锁定了冠心病研究
领域的另一个热门靶点——乙酰辅酶A胆固醇酰基转移酶(Acyl-
CoA cholesterol acyltransferase,简称ACAT)。当时有文献报道
认为,对ACAT的抑制能阻止胃肠道对外源性胆固醇的吸收,从
而与抑制内源性胆固醇合成的他汀类药物起到互补的作用。
先灵葆雅的ACAT抑制剂项目在启动后马上就遇到了麻烦。
团队科研人员精心设计出来的在纸面上看起来很合理的新型化合
物在一轮又一轮的生物测试中都没有呈现出预期的生物活性,令
人失望。一个有心的实验员,把本来应该丢进废料桶的副产物分
离纯化之后送去做了测试,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这个产率不
到5%的副产物不仅在体外生物测试中显示出了相当的活性,而且在高剂量的动物模型中也有一定的药效。如果说测试一个非设计
的副产物已经是小概率事件,那么这个副产物不但有体外的生物
活性,而且还有动物模型中的药效,就是小之又小的概率了。
先导化合物被意外地发现了。以这个有活性的副产物作为模
板,研究人员接着一轮一轮地设计新的化合物,试图优化这个先
导化合物。虽然这些新化合物对ACAT的抑制活性越来越高,但
是在动物模型实验中的效果(胆固醇下降)不见有什么增强,停
留在30%左右,远远低于适合临床开发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
下,公司高层慎重地评审了这个项目,认为该靶点与胆固醇的吸
收没什么相关性,决定停止ACAT抑制剂项目,将有限的资源投
入其他更有希望的项目上。公司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的研究结
果也证实了ACAT与胆固醇的吸收确实没有必然的联系。
辛辛苦苦做了几年的项目要下马,项目研究人员当然不高
兴,他们所能做的便是将这个项目的实验数据整理成文,争取在
科学杂志上发表。在整理这些数据和撰写论文时,研究人员经常
需要补充少量化合物及其数据。于是,在部门领导点头之后,一
名药物化学人员在项目被宣布下马之后又补做了2对(4个)新的
化合物,打算在生物测试之后,将这些新的数据填写到论文的表
格里去发表。尽管体外测试的结果跟预计的差不多,但在动物模
型实验中意想不到的一幕又出现了:其中两个新化合物的药效比
所有已知的化合物高出了很多倍。新的突破口又一次被意外地发
现了。
在对这个意想不到的补充化合物进行代谢研究时,药理研究
人员发现,该化合物所产生的药效可以持续很长时间,远远超过
根据它的体内半衰期所预计的有效时间。也就是说,当血液里药
物浓度下降至有效浓度以下时,它的药效却仍然存在。怎么会这
样呢?经过研究人员追根溯源的仔细研究后,在用药后的仓鼠的
胆管里发现了几个比药物本身活性更高的代谢产物。在新药研发
里,这样的好事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了这个可遇而不可求
的发现,团队的科研人员通过化学修饰,合成出了体内活性比原先的临床候选药物高出400倍的新化合物——益适纯(Zetia)。
因为益适纯也只是在胃肠道和胆管里来回周转,只有很少量进入
血液循环和身体的其他脏器,所以它的安全性也非常之好。
随着临床研究的顺利进行,公司开始着手准备向FDA报批申
请材料,可是项目团队的研究人员又犯难了:益适纯所作用的体
内生物靶标肯定不是当初立项时的ACAT,那到底是什么呢?在
正常情况下,FDA一般是不会批准生物靶标未知的新药上市的,益适纯又是一个例外,因为它的临床前动物实验与临床试验的结
果很有说服力,疗效显著,安全指数好,适应面广,与他汀类药
物能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后来先灵葆雅与默沙东合作研发益适
纯与舒降之的复方制剂,在合作过程中,两个公司的联合研究团
队也最终搞清楚了益适纯的生物靶标是PNC1L1——胃肠道里一
个重要的胆固醇输送蛋白。
那是益适纯上市(2002年)以后好几年的事了。
葆至能更上层楼
如果说每一个成功的新药研发项目都包含着一点幸运的因
素,那么益适纯的研发过程中幸运的因素就远远不止这一点点
了。但仅仅靠撞大运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严谨的科学态度与
实践,正因为如此,益适纯的研发团队不但歪打正着地创造出了
一个又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且还及时抓住了这些一闪即逝的机
会,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成功。
从机理上看,益适纯抑制胃肠道对外源性胆固醇的吸收,应
该能与抑制内源性胆固醇合成的他汀类药物起到互补的作用,所
以当益适纯还在临床试验阶段时,默沙东就拿着舒降之上门求合
作去了。
两种药物联合使用,最坏的可能性是出现药物相互作用
(Drug-drug interaction),不但药效会受到影响,还有可能出现毒副作用;最常见的结果是既不互补也不互损,1加1等于2;最
好的结果则是互补的协同效应(Synergistic effect),出现1加1大
于2的结果。益适纯与舒降之联合使用的复方制剂葆至能(商品
名Vytorin)就是这种最好的结果,非但没有相互干扰,而且还显
示了很好的协同效应。
科学是严格的。益适纯与舒降之联合使用可以有效地降低胆
固醇,并不等于也一定能降低冠心病患者心梗的风险。换句话
说,默沙东经典的4S研究结果并不能直接扩展到益适纯与舒降之
的联合使用,只有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才能说明问题,于是乎,又
一个长达9年的临床试验开始了。
2014年,美国心脏协会公布了默沙东制药名为“IMPROVE-
IT”的临床试验结果,数据显示,舒降之与益适纯的复合制剂葆
至能可显著减少高危冠心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益适纯与舒降之
的互补性使得葆至能非常适用于对他汀类药物敏感度较低的患
者,只要用相对较低的剂量就能将他们血液里的胆固醇控制在健
康的水平。葆至能可以同时抑制胆固醇的内源性合成与外源性吸
收,在高胆固醇和冠心病的治疗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过去的30年里,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比
例已经逐步上升到接近50%,在同一时期内,这个年龄组的心脏
病死亡率持续显著下降。
[35]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吸烟人口
的下降,饮食更为健康(至少在某些方面),心脏病治疗的改
善,心梗紧急治疗更为及时,等等。尽管我们很难把这些变化所
带来的效果一一区分开来,但是毫无疑问,服用他汀类药物所带
来的整体人群的胆固醇水平降低一定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2011年6月初稿于新泽西
2017年7月修改稿于上海第七章 “是药三分毒”的背后
从原创的顺尔宁到它的仿制药
是药三分毒,安全与有效是新药研发贯穿始终、相互依存的
两个对立面。
现在每一个药物的说明书上除了适应证与用药剂量之外,一
定会有好几条有关副作用的警告,严重的还会有“黑框警告”。就
拿最最常见的阿司匹林来说吧,在市场上这么多年了,大概没有
人还会认为服用阿司匹林有什么不安全的,但它的说明书上清清
楚楚地写着:服用此药有可能导致胃肠道出血。最近的一项来自
意大利的跟踪研究
[36]
数据显示,在18.6万长期服用低剂量阿司
匹林的人群里,胃肠道出血的有2300个病例(占1.2%),脑出血
的有1300个病例(占0.7%)。
安全指数:在药效与毒副作用之间
从辩证法的角度讲,能把人治好的东西也一定能把人治坏,就看你怎么治,治到什么程度。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破冰,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
基辛格博士在巴基斯坦访问期间对外称病住院三天,其实却在秘
密访问中国。消息公布之后,有传闻说基辛格当时真的病了,在
北京期间听从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到协和医院接受了针灸治疗,结
果针到病除,由此引发了全球范围的“针灸热”。当时针灸被说得
神乎其神,很重要的一条理由是,它号称绝对没有副作用。其
实,这种说法既不符合辩证法,也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当年金
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还没有流入内地,要不然以针刺穴而置人于死地的武林高手和民间故事应该是信手拈来的。针灸治病的机
理目前还不清楚,但相信它有(不只是心理)作用的人必须承
认,针灸一定要通过改变人体内的某个生物过程才会有疗效。这
个生物过程既然能改变人体的状态,从病态变回到正常态,那么
它一定也有可能反过来,把一个人从正常态变为病态。
药物治疗是用化学物质(包括各种无机盐、有机小分子和生
物大分子等)来改变人体内某个特定的生物过程。在任何一个时
刻,人体内都有成千上万个化学反应在同时进行着,这是维系生
命所必需的。所谓“正常态”就是由这些化学反应而决定的生物过
程在一定范围内的波动。从表征上讲,心跳不能太快也不能太
慢,血压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等等;表现在分子水平上,就是
功能性蛋白质(包括受体、酶、离子通道、转运蛋白等)的表达
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各种代谢和循环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
旦超出了这个正常范围,就会出现“病变”,人体也就进入了“病
态”。
造成人体病变的原因有很多,比如2型糖尿病,是因为人体
内的葡萄糖代谢发生了紊乱,使得血糖持续升高,从而引起一系
列严重的并发症。通过服用西格列汀等新型糖尿病药物,可以改
变糖尿病患者的葡萄糖代谢,把血糖降下来,将其控制在正常范
围内。
[37]
但是,如果哪一个药物把血糖降得太多了,就有可能
给病人带来生命危险。所以制药界还有一句行话,“剂量造成毒
药”(Dose makes poison),什么东西吃多了,都有可能给身体带
来不良后果,药吃过量了,当然就更是如此了。
怎么吃药才算安全呢?制药界定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
——安全指数(Safety index),有时也称“治疗指
数”(Therapeutic index),或者“安全窗口”(Safety window),它是最高安全剂量(又称最高无副作用剂量)与最低有效剂量之
间的比值。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临床试验药物的最低有效剂量是
每千克体重2毫克,而在临床试验中没有观察到副作用的最高剂
量是每千克体重40毫克,那么这个试验药物的安全指数就是402=20(一般用“20X”表示20倍的意思)。安全指数是根据临床
试验的数据计算出来的,是参与临床试验人群的统计数值。对于
不同的副作用,安全指数一般来说是不一样的,比如引起轻微头
疼的指数是10X,而引起血压升高的指数则可能是50X。对于不
同的人种、不同的性别以及不同的年龄组,同一种药物的安全指
数也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落实到个体病人,每种药物的安全指数
还会有上下波动,但是绝大多数都应该在统计误差的范围之内。
在原创新药的研发过程中,安全指数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杆。安
全指数越高的药,用药的允许误差就越大,适用的人群就越广。
一种新药若能被国家监管部门批准用于婴幼儿,它的安全指数一
定是很高的,默沙东的原创新药顺尔宁(Singulair
TM ,药名孟鲁
司特[Montelukast sodium])就是少数几类被批准用于治疗婴幼
儿哮喘病和过敏症的药物。
哮喘病:在成年人与婴幼儿之间
哮喘病(简称哮喘)是一种很常见的慢性病,也是少年儿童
中最多发的慢性病。
哮喘(Asthma)的英文词源于古希腊文,意指“急促的呼
吸”,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50年希波克拉底的描述中。几百年后,古希腊医学家盖伦撰文,第一次提到了哮喘是因部分或整个支气
管阻碍所造成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8月在其官方网站上
更新的数据,目前全球哮喘病患者大约有2.35亿,与哮喘相关的
死亡有80%发生在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
中心官方网站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成年哮喘病患者人数
接近2000万,平均每12人中有1人患病;儿童哮喘病患者人数约
700万,平均每11名儿童中有1人患病。年龄组18岁以下的发病率
(9.6%)明显高于年龄组18岁以上的发病率(7.7%),而发病率
最高的年龄组是5~17岁,接近11%。中国哮喘联盟发布的一份报
告显示,我国哮喘病患者多达3000万,发病率高达1.24%,而在
众多的哮喘病患者中,儿童就占600万,发病率为1.97%,这意味着每100名儿童中就有2名哮喘患者。由于统计数据不全,加上一
些偏远地区的医疗条件较差,应当还有相当多的哮喘病患者尚未
被确诊,所以实际患病人数估计远远超出4000万,其中约有700
万儿童饱受哮喘困扰。在环境污染严重的今天,哮喘的发病率还
会不断上升。
哮喘病是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重要疾病,如果治疗不及时,不规范,哮喘的急性发作甚至可能致命。我们这一代人都非常熟
悉和喜爱的一代歌后邓丽君女士就是因为哮喘突发,抢救不及时
而离世的。2002-2007年,美国每年用于治疗哮喘病的费用平均高
达560亿美元,经济损失巨大。哮喘病多发于学龄儿童中,全美
国的中小学生因为发哮喘而不能上学的天数每年累计大约有1500
万天。
哮喘病是一种支气管慢性炎症性疾病,这种慢性炎症导致孩
子的气管过分敏感,当受到各种因素的刺激时,过分敏感的气管
发生反应,就会出现哮喘症状。发病内因包括儿童本身特应性体
质、遗传特性等;外因则包括空气污染、食物过敏、营养不均、宠物过敏等。其中环境污染的关联最为突出。PM2.5被认为会导
致咳嗽、呼吸困难、肺部功能降低、加重哮喘等疾病。这些细小
颗粒通过呼吸道,部分没有被过滤掉的就沉积在人体里,从而危
害健康。另外,季节变换时,尤其是春季,也是儿童哮喘的高发
期,会出现反复发作性喘息、胸闷、咳嗽乃至呼吸困难。患儿不
能参加正常的学习和课外活动,给家庭带来了较大的身心负担。
从20世纪开始,支气管扩张剂一直是治疗哮喘病的重要手
段,主要有抗胆碱类药物(Anticholinergic agent),如溴化异丙
阿托品(Ipratropium bromide)和β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β2
adrenergic receptor agonist),沙丁胺醇(Albuterol)和特布他林
(Terbutaline)等药物。直到20世纪60年代,医药学家们才发现
哮喘不只是单纯的支气管挛缩,而是一系列的炎症反应,因此才
将消炎药加入哮喘病的治疗中。目前,以顺尔宁(孟鲁司特)为
代表的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可以抑制气道炎症,降低气管敏感性,减少病毒诱导的间歇性喘息,尤其适用于治疗同时患有过敏性鼻
炎的哮喘。
顺尔宁:在大胆创新与谨慎验证之间
20世纪30年代,两位澳大利亚生理学家从豚鼠的肺部发现了
一类“慢反应物质”(Slow reacting substance,简称SRS),到了70
年代,类似的“慢反应物质”在人的肺部也被发现了,而且有迹象
表明,这些“慢反应物质”很可能在哮喘的发病过程中起着很重要
的作用。尽管来源很有限,稳定性也不好,但很多制药公司还是
开始了对“慢反应物质”的研究,默沙东也不例外。
直到70年代末期,这些“慢反应物质”的结构才被逐一确定下
来,并被统一命名为“白三烯”
[38]
(Leukotriene,简称LT)类化
合物,随后完成的人工全合成又解决了来源短缺的问题,使得白
三烯的研究进一步深化,而白三烯受体拮抗剂有可能用于哮喘病
治疗这一大胆的假设也为更多的医药研究人员所接受。要知道,当时白三烯的受体还没有被发现,直到90年代末期,默沙东的第
一个白三烯受体拮抗剂药物顺尔宁上市后,白三烯的受体才首次
被提取出来。
在没有纯化的白三烯受体的情况下,所有实验都只能在细胞
或组织里进行,通量低,稳定性也差。面对这样的挑战,位于加
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郊的默沙东实验室福斯特研究所
(Merck Frosst)的科研团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将第一代的
两个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候选药物先后推上了临床试验,一个做口
服药,另一个做喷雾吸入制剂,但结果差不多,都不尽如人意。
这两个化合物虽然都有一点点统计意义上的药效,但远远没有达
到临床应用的标准。面对挫折,默沙东蒙特利尔的研究团队决定
寻找活性更高的白三烯受体拮抗剂,以期达到显著的临床效果。
1989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第二代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候选药物
进入了临床试验。因为活性和口服生物利用度的大大提高,在为期6周的药效试验中,哮喘病患者的肺活量有所提高,肾上腺素
受体激动剂的使用减少,喘息、胸闷乃至呼吸困难等典型哮喘病
症状都有了明显改善,实现了临床的概念证明(Clinical proof of
concept,简称Clinical POC)。预期的药效达到了,但副作用也
随之而来。在高剂量的大鼠安评试验中,这个候选药物引起了意
想不到的肝肿大,没有了足够的安全指数,临床试验也只好立刻
下马了。
进一步的毒理研究发现,大鼠的肝肿大是由于肝脏过氧物酶
体(Peroxisome)的增殖引起的。有没有可能找到既有明显药
效,又不会引起肝肿大的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呢?带着这个疑问,默沙东实验室的科研人员重新回到实验室,继续埋头苦干,在安
全与有效的夹缝里,寻找新一代的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功夫不负
有心人,1991年默沙东实验室的第三代第四个白三烯受体拮抗剂
候选药物进入了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口服剂量从2毫克一直到
800毫克都没有发现副作用,而有效的口服剂量只要5~10毫克左
右,安全指数之高可见一斑。在随即展开的儿科临床研究中,这
个候选药物的咀嚼剂型在婴幼儿患者中也同样显示了良好的疗效
和安全性,而且不影响婴幼儿的生长速率。
临床研究的好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了默沙东福斯特研究所,为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的研发一起辛勤工作了18年的科研团队又一
次聚到了小会议室里。他们再一次绞尽脑汁,为这个即将诞生的
抗哮喘新药命名。热议之后,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个未来的新药
叫作“孟鲁司特”(Montelukast)
[39]
,以纪念它的诞生地——蒙
特利尔(Montreal)。1998年2月,顺尔宁(孟鲁司特)上市,被
批准用于成年人以及6~14岁儿童。2000年6月,顺尔宁又被FDA
进一步批准用于1岁以上的婴儿患者。
等效性:在原创药与仿制药之间
2012年8月3日,默沙东原创的用于治疗哮喘与过敏的品牌药孟鲁司特的化合物发明专利在美国到期了。
[40]
就在同一天,FDA批准了第一个孟鲁司特的非专利仿制药(Generic drug)。 [41]
从原来的独家生产,进入了多家竞争的新阶段。竞争无疑会
给消费者带来益处,但是大家自然而然地会问:仿制药与原创药
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仿制药与原创药里的有效成分在分子的水平上是完全一样
的,也就是说,有效成分是同样的化学分子。但是,尽管仿制药
里含有相同等量的有效成分,而且纯度检验也达到要求,但还是
有可能在疗效和副作用上与原创药有所不同。如何把一个化学分
子做成药剂还是颇有讲究的。
一般来说,原创药物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专利是化合物发
明专利,做仿制药这个专利是绕不过去的,所以必须等到这个专
利有效期届满。但是所有的原创药物除了化合物发明专利之外,一定还会有工艺流程的专利、晶型的专利、制剂的专利等,而且
它们的有效期都会在化合物发明专利之后,比如孟鲁司特的口服
液制剂(Oral granuales sprinkle formulation)的发明专利要到2022
年才到期。
这些“二线专利”虽然给仿制药的生产设置了壁垒,但它们的
保护是有限的,通俗地讲,就是可以“绕过去”的。首先,仿制药
的生产厂家会建立自己的工艺流程。由于工艺流程的不同,生产
出来的有效成分尽管在纯度上达到了要求,但是在杂质分布等其
他指标上很难做到与原创药完全一样,如果引进了新的主要杂
质,就必须做鉴定和安评。工艺通过了,还要挑选专利保护之外
的晶型。不同的晶型在体内溶解和吸收的速率是很不一样的,如
果你不信,就拿点绵白糖和冰糖放在水里试试,虽然都是糖,但
溶解的速率相差很大。原创药的专利晶型在溶解性、稳定性和生
产成本等各个方面肯定都有优势。仿制药的生产厂家没有别的办
法,只能在其他的晶型里挑选,然后通过制剂的研究,争取达
到“生物等效”。所谓生物等效性,就是仿制药与原创药的临床药代动力学比
较数据。为了保证仿制药与原创药有同等的药效和安全性,仿制
药的生产厂商必须在报批时向药监局提供“生物等效性”(Bio-
equivalency,简称BE)的临床数据。BE这个术语近两年在国内
医药界变得非常流行。只有在仿制药的药代动力学指标进入了原
创药的误差范围之内,才能宣称该仿制药与原创药具有“生物等
效性”,药监局才会批准上市。这是一个相对小规模的临床试
验,所以研发仿制药的成本远远低于原创药,药品的价格也就会
远远低于原创药。大量低价仿制药的上市可以让更多的患者获得
及时的治疗,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医保环节的经济负担。
因为生物等效性的临床试验是短期的,而原创药在化合物发
明专利到期之时,已经积累了大量长期临床使用的数据,医药人
员对其药性、剂量、适用人群、可能发生的副作用等重要参数都
有很好的了解,所以用起来更放心一些,尽管在价格上要贵一
些。不光医药人员如此,广大患者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有
这个倾向,所以,拜尔生产的阿司匹林到现在仍旧是药房里最受
欢迎的。
固定剂型:在体重与剂量之间
目前,顺尔宁的剂量有10毫克和5毫克的片剂,适用于成年
人;有4毫克的片剂,适用于儿童;还有婴儿用悬浮液,出生6周
以上的婴儿就可以用了。
所有新药在临床前的动物研究期间,其用量都是按照实验动
物体重严格计算的,无一例外。药代动力学研究(药物进入体内
后都去哪了?)必须按体重计算用量,药效学(药物进入体内后
都干了啥?)也必须按体重计算用量。这样做有利于建立剂量的
相关性,消除因为体重不同而带来的不确定性,也有利于不同种
类的实验动物之间的外推和换算。但是,一旦进入临床研究,按
照体重计算剂量的可操作性就没有了,药房是不可能给前来配药
的患者先称一下体重,然后计算出相应的剂量,当场配制药物的,所以只能是一个或几个预先设计好的固定剂量。
在临床研究的前期,因为健康的志愿者或患者人数相对较
少,挑选可以比较严格,特别瘦小,或是特别肥胖的人可以不入
选,所以用平均值(一般男性按60千克,女性按50千克)计算也
不会有大的出入。在做人体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时,还会有意识地
包括不同体重的受试者,获得药物与体重的相关性,以便在临床
研究的后期确定不同年龄组的不同剂量。
就拿顺尔宁来说,成人的用药剂量确定在5毫克和10毫克两
个固定剂量,但是根据药代动力学的数据,5毫克用于儿童保险
系数不够大,因为儿童的体重差别是很大的,为此,默沙东专门
开发了4毫克的片剂。你也许会问:5毫克与4毫克只差1毫克,真
的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如果说是100毫克与99毫克,那倒真是没多大差别,因为相
对误差才1%。但是5毫克与4毫克就不一样了,相对误差已经达到
了25%。一个1岁的哮喘患儿,本来身体发育就受到了影响,体重
偏低,再多吃25%的药物,结果就不好说了。
开发5毫克与4毫克两种片剂也把默沙东的化学工艺和制剂研
究水平推到了极致。试想一下,生产100万片4毫克的顺尔宁药
片,必须把每一片有效成分的误差范围控制在3.6~4.4毫克之内
(±10%),需要多高的工艺精度?中国目前的化学工艺研究进
步很快,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够以可持续的“绿色化学工艺”生
产出剂量精准、生物等效的优质仿制药。
由于像顺尔宁这样全年龄组的抗哮喘新药的使用,当今的治
疗手段可使接近80%的哮喘患者的病症得到非常有效的控制,使
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不受影响。国际卫生组织把每年5月份的
第一个周二定为世界哮喘日,旨在提醒公众对疾病的认识,提高
对哮喘的防治水平。
2012年12月初稿于上海2017年12月修改稿于新泽西OEBPSTextpart0011.xhtml
第八章 凝结中国科学家毕生心血的HPV疫
苗
从诺贝尔医学奖的基础研究到制药公司的创新产品
癌症在很多人心目中可能还是“不治之症”的代名词,尽管近
年来,随着基础医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医药界对于癌症的认识已
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对于癌症的治疗和预防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
展。2006年,默沙东投放市场的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简称HPV)疫苗佳达修? (Gardasil
)就是其中一个通过
抗HPV感染而预防包括子宫颈癌(Cervical cancer)在内的多种疾
病的有效疫苗,这也是一个凝结着中国科学家周健博士毕生心血
的疫苗。
十年“钓鱼”,豪森教授找出子宫颈癌起因
大多数癌症的起因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女性子宫颈癌是一
个例外。早在1974年,德国海德堡癌症研究中心的海拉德·豪森
(Harald Hausen)教授就提出了HPV长期慢性感染会导致子宫颈
癌的假设。这个大胆的假设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因为
当时子宫颈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纯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上。
豪森教授独辟蹊径,率领他的研究小组,潜心寻找子宫颈癌
细胞中人乳头瘤病毒的遗传物质DNA。他认为这些在癌细胞中的
病毒DNA很有可能处于长期的休眠状态,并不一定会复制新的病
毒体,这给他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豪森研究小组采用了一种俗称“钓鱼”的研究方法,把人工合成的已知DNA片断做上标
记,通过细胞内杂交,设法提取病毒的DNA。他们成功地从脚底
疣的细胞中找到了HPV的DNA片断,后来在皮肤疣的细胞中也找
到了。但是,当他们将同样的方法用于子宫颈癌细胞时却失败
了,没有找到HPV的DNA片断。豪森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没有气
馁,也没有怀疑他们当初的设想。考虑到病毒DNA不断变异的特
性,他们改进了传统的“钓鱼”方法,扩大搜索范围,经过十多年
的艰苦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钓到了“大鱼”,在子宫颈癌的活
体切片里找到了HPV的DNA片断。
1983年,豪森教授首次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立刻引起学
术界的高度重视。随后的研究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
是由于HPV的持续性感染引起的,并且其中大约有70%的病例是
由HPV家族中的HPV-16和HPV-18这两种型别的病毒感染引起
的,而这两种型别正好就是豪森研究小组最初发现并克隆的型
别。豪森教授的这项研究证实了HPV的构成,阐明了HPV的致癌
机理,以及影响病毒存活和细胞转化的因素,为预防和治疗妇女
子宫颈癌奠定了理论基础。2008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
员会决定授予豪森教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表彰他的研究成
果对于人类健康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持续感染,人乳头瘤病毒危害深远
HPV是一种属于乳突病毒科的乳突淋瘤空泡病毒A属,是球
形的DNA病毒,目前已经发现了200多个型别,其中至少有40个
型别是通过性接触在人群中传播的。HPV病毒的其他传播途径包
括密切接触、医源性感染(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防护不
当,造成自身感染或通过医务人员传给患者)和母婴传播(婴儿
通过孕妇产道时的密切接触)等。在已知的HPV型别中,大多数
不会引起被感染者的任何症状,而且感染期也相对短暂,被感染
者能在1~2年之内自愈,目前尚未发现长期遗留的不良影响。但
是,有少数被感染者会发展成持续性的感染,造成人体皮肤黏膜的鳞状上皮增殖,表现为寻常疣、生殖器疣(尖锐湿疣)等症
状,属于低危型HPV感染。低危型的HPV感染率非常普遍,关于
女性生殖道HPV感染的流行病情,据2003-2004年来自美国的国家
健康和营养研究课题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14~59岁的HPV总感
染率接近27%,也就是说,在这个年龄段里,每四个女性中就有
一人被感染!而在卫生条件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里,HPV的感
染率还会明显高于这个数字,所以HPV感染对女性造成的危害大
大超出了先前的估计。根据2007年发表的中国HPV感染的筛查报
告,[42]
在子宫颈癌高发的农村地区和大城市的5218名妇女中,20~54岁妇女的生殖道高危型HPV平均现患率相近,分别为
14.6%和13.8%,显著高于世界发达国家同年龄的现患率(5%~
10%)。尽管没有子宫颈癌的威胁,男性也同样被HPV感染所困
扰,生殖器疣会带来生活上的诸多不便,而且HPV也是肛门癌和
阴茎癌的主要感染源。
在被HPV持续性感染的女性中,有5%~10%会逐步恶化,引
起宫颈鳞形上皮不同程度的病变,发展成高危型的HPV感染,整
个过程通常要10~15年时间。这些进一步的病变有可能最终导致
恶性的子宫颈癌,成为危及妇女生命的恶性疾病,发病率仅次于
乳腺癌,居妇科恶性肿瘤的第二位。著名香港艺人梅艳芳就是因
患子宫颈癌英年早逝,年仅40岁,是演艺圈和众多粉丝的巨大损
失。2002年,由HPV感染而引发的癌症新病例估计超过56万,居
所有癌症感染源的首位。宫颈癌是女性中第四大常见癌症。根据
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官方网站的预计,2019
年美国将会有1.3万多例宫颈癌的新病例,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将超
过4000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数据,在全球范围内,2018年宫颈癌新发病例估计为57万例,占所有女性癌症的6.5%,其中大约90%的宫颈癌死亡发生在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2015年中国癌症统计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宫颈癌新发病例约
9.89万例,死亡人数约3.05万,发病率和死亡率呈明显的上升趋
势,且子宫颈癌发病年轻化,由此可以推测高危型的HPV感染在
中国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精诚合作,中澳联手构筑病毒“空心汤团”
既然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是由高危型HPV持续感染引起
的,而防止病毒感染最有效的方法是接种疫苗,那么如果能研发
出预防HPV感染的疫苗,不但可以有效地降低子宫颈癌的发病
率,而且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与HPV感染相关疾病的传播。
本着这样一个基本的科学理念,澳大利亚墨尔本沃尔特伊莱扎医
学研究所的免疫学家伊恩·弗雷泽(Ian Frazer)教授与中国病毒
学家周健博士合作,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HPV疫苗的研究。
1989年,已经小有名气的伊恩·弗雷泽教授到英国剑桥大学学
术休假。在那里,他幸运地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这就是来自
中国的青年访问学者周健博士。日后,功成名就的弗雷泽谈起这
段往事时非常感慨地说:“我在剑桥大学的学术休假,并没有学
到多少计划中想学的干细胞知识,却幸运地遇见了周健。我们开
始合作研究HPV并探讨研制疫苗的可能性,周健的贡献在病毒
学,我的贡献在免疫学。”
[43]
两人在剑桥的相遇是短暂的,弗雷
泽在返回墨尔本之前,热情邀请周健夫妇去澳大利亚工作。
周健博士1957年出生在杭州,中学毕业后在当地一家工厂里
做工人。1977年恢复高考,周健考入温州医学院,成为一名本科
生,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并于1987年获得河南医科大学病理学
博士学位。在北京医科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一年之后,他前往
英国剑桥大学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免疫学与癌症研究中心肿瘤病
毒实验室做访问学者,并与弗雷泽相识。
1990年,应弗雷泽教授的邀请,周健博士带着妻儿来到澳大
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免疫实验室,和弗雷泽共同研究HPV。起初的
大半年里,他们的合作研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1184KB,137页)。